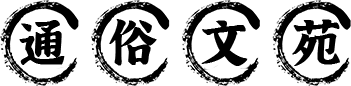第四十七回 养蚕有技术缎绸靠绝活 黑帮劫丝厂袍哥暗收场
词曰:
日日深杯酒满,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,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,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见在!
——《西江月》
话说贤龙之妻阿女生了有秀,全村人都来贺喜,满月后,阿女督促贤龙道:“你在何国玉丝厂当师傅,报酬又少,不如把柏垭场杜朝霞几十担干茧租来与杜家街杜有举合伙缫丝,等丝卖了再付钱。”贤龙听了妻子的话,同杜朝霞在黎家罐几间空房里缫起了丝。
来年四月,见人说成都府的丝好卖,他同杜有举,置办土丝起来,一般的土丝先求了买主出售,上等的土丝用麻布捆好,拣个日子装了篾箱儿,到了成都府。岂知成都,自交夏以来,日日淋雨不晴,并无一毫暑气,发市甚迟。迟延半月有余,幸喜天色却晴,有土丝商要买上等的好丝。来买时,开箱一看,只叫得苦。原来成都历沴日前雨湿之气,这土丝放置在客栈一楼环房,受湿遭了霉菌危害,土丝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,揭不开了。只剩下少部分不坏的,能值几何?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,本钱一空。真是:
往日彩虹今难见,气变高寒三伏冬。
土丝遇涝遭虫叮,赔了本钱又受穷。
却说贤龙与杜有举在成都做土丝生意算倒了八辈子霉,算了算去几十担干茧搭上去, 自己掏腰包建缫丝房,备工具,人工 …… 今后的路该怎样走?正踌躇间,忽见何国玉上门拜访。“老弟呀!听说你这次出门不悦,亏了本钱……”,“别提了,生意没做成,还拉了不少的债,这些年我的生意很不顺心呀!那些年我和妻子在渝州做土丝生意,虽差点命归黄泉,不过遇上了贵人,现打听我的朋友渝州刺史副官谢安已不在渝州,据说他已回到北京。现在出远门做生意土匪多,风险大,……”
贤龙很内疚,“对不住你了,望你原谅……”
国玉安慰道:“不说那些丧气话,我来的目的,是想把我的丝厂租给你,每年由你给点租金就行了!其实我有的是庄子,不靠这个丝厂,老弟,请相信我!” 贤龙听了,跪下道:“太感谢你呀,你真是我的福星!”
“快起来,我是很欣赏你的为人,对人诚恳憨厚,你现在还住在榨房嘴茅房里,好好干, 等经济条件好转,好好改造一下住房”,阿女抱着有秀,也走出门来致谢。
这下黎贤龙可以大显身手,干脆全家人就在丝厂生活,养蚕、缫丝、织绸,要干得大干一场,全程茧丝绸工序直接出成品,……
年末的百日福、蚕花娘娘的诞辰,贤龙得好好准备。因为每年的腊月十二,正是三素元君朝真之日,也是蚕花娘娘诞辰。蚕花奶奶也就是蚕花娘娘、蚕花姑娘,又称为“马头娘”,或称“马头神”。后人庙会塑了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姑娘,放在庙中供奉,正式称为“马鸣王菩萨”。自然相关的祭祀活动繁多,蚕的一眠、二眠、三眠一般都有相应活动, 其中一个就是“摸蚕花奶奶”的活动,在每年清明庙会祭拜蚕种时进行。
俗话曰:“轧发轧发,越轧越发”,或是“摸发摸发,越摸越发”。嗯,其实这项活动就是摸乳房,头清明节祭祀娘娘这天的庙会上,谁家姑嫂被摸得乳房发痛,她家这年蚕花会“发”。
这一天,贤龙要给蚕宝宝做“生日”,这天要“腌”蚕种,还要磨粉做“茧子圆子”, 用来祭祀灶君。贤龙、阿女这天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祀灶家菩萨,灶山上供起了“茧子圆子”,还有甘蔗、荸荠、桔子等鲜果,仪式自然是插烛点香,祈求灶王爷能保佑自家来年“蚕花廿四分”。茧子圆子是用糯米粉做的,大小形似茧子,分青白两种。青圆子是把石灰水炝过的南瓜叶子煮烂捂进糯米粉里做成的,白圆子纯用糯粉。“茧子圆子”具阿女说:青色,象征桑叶,白则代表茧子。寓意吃青(桑叶)吐白(蚕丝)。 给蚕宝宝做生日为什么要请司灶之神保佑而不是请蚕花娘娘呢?那就不必深究。
贤龙夫妻祭拜过灶神,农家紧着做的是一桩重要的蚕事——腌种。贤龙把自家留的蚕种拿来,据悉:采茧第十八天茧子出蛾子,雌雄蛾交配后,把雌蛾捉在预备好的“夏布”——这是一种用苎麻纺成的布,硬爽通气——片上产卵,等蚕卵布满整片夏布,把夏布放到温水里浴一浴,漂去了瘪卵,然后把整张蚕种收起,挂在通风的地方。到腊月十二这天再把蚕种取下来,撒些盐粒在上面,用布袱包起,为“腌种”,有《腌种歌》这样唱:
腊月十二蚕生日,家家腌种不偷闲。
有的人家石灰洒,有的人家松盐腌。
还有人家天腌种,高高挂在屋廊檐。
通风透气防鼠剥,不怕日晒不怕寒。
十二子时来腌起。腊月廿四卯时悬。
收落蚕种掸落盐,轻轻放在竹筛面。
提来一桶春雨水,百花汤里潭格潭。
切忌外面日头晒,半阴半凉自家干。
蚕种“腌”到腊月二十三日,这天是送灶家菩萨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日子。
贤龙送过灶君之后,就把布袱里“腌”过的蚕种取出,轻轻掸去上面的盐粒,去清水河滨里漂洗一下,再把它挂到通风的地方晾干收起,第二年谷雨时节就可以收蚁养蚕了。
很快到谷雨了,布子上的蚕籽隐隐显青了,提示要“焐”种了。于是,阿女就把“布子”寻一块软布包好,贴肉焐在胸口,连身子也不敢多动,呵护“头生儿子”一样仔细, 过去七八天,感觉得到小蚕宝宝在蠕动了,才小心翼翼从胸口解下“布种”,用鹅毛把小蚕轻轻刷到用桃花纸糊起的小匾里。俗话说“小蚕靠火”,蚕室里要生一个炭火钵头,防着小蚕宝宝挨了冷,小蚕宝宝吃的自然是挑选过的嫩桑叶,阿女用专门的叶刀切成发丝似的细条来喂。碰着落雨天,阿女采来的桑叶还要一张张用干净毛巾正反揩干才下刀切,真正像管“头生毛头”一样。
贤龙阿女夫妻是养蚕能手,当然知道蚕要经过四个“眠”期——它的一个生命过程中间要蜕四次皮,先后分别叫做头眠、二眠、三眠、四眠,蚕养到大眠已是壮蚕了,这时就要分匾或在大门间里甚至廊檐头搭地铺喂养,因为此时蚕宝宝日长夜大,就像“朝头囡儿” 胃口特别大,桑叶再不用捋叶连枝带叶放下去喂饲就可以了,此时听得见的就是仿佛下雨似的“哗哗哗”一片蚕吃叶的声音。这样过去七昼时,一条条蚕宝宝身体颜色渐渐变浊, 预示宝宝要“上山”了。蚕宝宝每次“眠”时不吃不动。当蚕要吐丝时就会爬上贤龙预备好的稻草扎成的“蜈蚣簇”上。之后吐丝结茧,贤龙一家和邻居帮忙的就等着采茧子。
采茧子的邻居称阿女为“蚕花娘娘”因为她举止端庄,像个女神,大家要她讲故事。这阿女也不客气,就讲起了蚕宝宝的传说:
她跟大家说:“太古的时候,有个没娘的女孩,父亲上了西番战场。一个家只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和一匹小公马,寂寞时她就和小公马絮絮叨叨说话。她天天盼着父亲回家,但杳无音信。有一次,她抚着小公马的脑袋自言自语:‘小伙伴,你如果能去接我老爸来一趟家,我就把自己嫁你——能么?’女孩本是说着玩的,可是那匹小公马当天不见了身影。 正当女孩子为小公马的突然失踪焦虑不安时,忽然看见父亲竟然骑着小公马来到了大门口。女孩说不出的那个高兴啊,为感谢小公马,她喂它最好的食料。可是奇怪,小公马却一碰都不碰,只对着姑娘长嘶不已。女孩子忽然想起了自己对小公马的戏言,她告诉了父亲。女孩的父亲一下惊呆了,以为是妖祸作祟,他担心妖祟祸害女儿,一铜棍打死了小公马, 把马肉做了干糗,当做回程时路上的干粮,把剥下的马皮晾在院子一棵树下。 这天,老爸回战场去了。女孩子更孤单了,因为本来她还有小公马伴着她,可是现在它没了,对着院子树底下还晾着的马皮,暗暗垂泪。正当神情恍惚,忽然看见那张马皮‘倏’地展了开来,把女孩的一个身子紧紧裹在了里面。好几天之后,邻居们都奇怪怎么没见姑娘的身影,大家打开了她家院子门,看见的是树下被马皮紧裹着的姑娘尸体,顿时都惊呆了,最终只好就地把她和马皮一块儿在树下埋了。天渐渐暖和起来,乡邻们发现姑娘院子里那棵树上爬满了胖乎乎的虫子,这些虫子吃着树叶慢慢长大,后来吐出洁白的丝,后来又结成一颗颗雪白的茧子。乡亲们都说这是姑娘和马的化身,把它叫做‘蚕’,又说那棵树附着丧身的姑娘的灵魂,因为‘丧’和‘桑’同音,就把那棵树叫做了‘桑’树。雪白茧子能缫丝织衣,乡亲们每年就养起蚕来了,为感念姑娘造福世人,就敬她为蚕神,给她塑像建庙,让她头戴金凤冠,身穿花衣裳,打扮得像个新娘子。人们年年到庙里给她上香摆供,祈祷她保佑自己家蚕事兴旺。据说还十分灵验呢!”
在回龙村黎贤龙家里,看着满屋子白白胖胖的老蚕,贤龙、阿女觉得一个月时间付出的辛苦都值得了。
贤龙将原来丝厂的炕茧房和缫丝房略加改进,把活茧炕成了干茧进行缫丝,需要制备的是手工织绸机,要买,价钱非常昂贵,唯一的办法请了三台的老木匠朱彤鲜来家制作,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几台织绸(布)机就大功告成。
操作织绸,贤龙可算是能手,织绸与织布都一样操作,就是经过作缯、闯杼、吊机、栓绸、织绸、了机等十几道工序,因此,除阿女能行,玉女、幺女还有其他妇女都得要学, 很多重要工序那阿女处处指导。
阿女道:“织绸时,机身要有一定的倾斜度,你们端坐在织绸机这一端的绸柱前,双脚踏板上下交替,双手轮换着操纵机杼和梭子,只要双手翻飞,穿梭往复,娴熟的动作如弹钢琴一般美妙……”
贤龙的丝厂办的有声有色,他有创新精神,除单纯的植桑、养蚕、炕茧、缫丝,现在又办起了织绸厂。他把不能缫丝的双宫茧,乌茄茧,薄壳茧,用来绷“绵兜”——丝绵。绷“绵兜”要数阿女,阿女把二三斤上面说的几种茧子装进一个纱布袋放进煮锅,加水浸没茧袋,放进二两老碱,烧至水滚,不停翻动茧袋,让袋内的茧子熟得均匀,如果是剥壳茧子,还要倒一调羹菜油进去,这样做出的“绵兜”才油亮滋润。二是绷——看着茧子煮“熟”,绷“绵兜”的玉女去袋子里拿一个出来扯一扯,如果丝头能拉长了,便把一袋茧子连开水倒进架起的一个木脚盆里,搁脚盆的木架上插着弯成弓形的竹绷。绷“绵兜”的玉女坐在脚盆前,拿一个烫在桶里的茧子翻转,剥去里面的蚕蛹,随即把茧子绷开来套在伸直的四根指头上,套得七八个茧子就成一绡,褪下,再绷到竹弓上,这弓竹张开有大小,剥出的绵兜大的叫“纩”,小的叫“小纩”。三是晒: 一绡绡“绵兜”用线穿起,晾在道地的竹竿上,直到晒干收起。
翻“绵兜”要絮进衣裤或成被絮,还有一个“翻”的过程。“翻绵兜” 几乎每家每户入冬都需要絮衣被了。用两张方桌接了起来,把要絮的衣服或被头夹里翻转在外铺放桌上,端正舒齐,两个女士把一个绵兜一个绵兜对着拉开绷松扯大,按衣袖、前襟、后背大小成形,一绡绡贴上去,视绵袄厚薄或二三绡或五六绡,然后用缝针粗粗缀一缀,再把衣服面子翻过来,之后缝口,襟片、后背或袖子每处再钉几行线。便是丝绵衣,它轻、暖,。翻丝绵看似简单,其实却是个技术活,一绡绡丝绵白若凝脂松如絮云,蓬松匀净,这全靠两位女士默契配合,完全手上功夫。丝绵衣被轻软暖和,穿过一年,拆出衣壳子,里面丝绵晒一晒,逐层绷一绷松,隔两三年,添一层新絮夹在旧絮中间,又复是新袄或新被子。
把蚕蛹晒干,卖出去,变成钱。算来,除正统的丝绸外,丝绵衣、丝绵褥、丝帽、还有蚕蛹等,其经济收入也不赖。
除此之外,贤龙还有一件发明,且是值钱的绝活,他把一种活化石一样的丝绸图案, 进行“先染后织”,在上机织布之前,颜色就由贤龙亲手染在蚕丝经线之上。染料缸散发着中药味,不同色彩的染料,都是由当地的花卉草根添加靛石矿料,浸泡而成。扎染这些蚕丝是非常细致繁琐的手艺。染色如同“召唤”,就好像画家在调色盘里召唤画面,雕塑家在花岗岩里召唤他的人物,也好像诗人捡拾那些石破天惊的词语,召唤音韵、节奏与喷涌的情感。黑红相间,蓝白间错,黄赭互衬,丝线成股扎起,染好之后再细细分层,自然形成的色晕如西斜的光线照临夏末秋初的维族小院,树上杏桃累累,姑娘的耳坠闪烁宝石的光辉,小伙与老爹爹手里的热瓦普琴发出极为欢快的弹奏……这些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图案,贤龙早就在心中一一描摹。如今,他默默替每一络丝线编了号,而后上织机的过程,无非是把词语织成诗篇,把色彩的丝缕织成绸布上的云霞。
“咣当,咣当,”贤龙手中的牛角梭子已经被手泽浸润成深乌色,这深乌里又泛着酒液 般的深红。只见他的梭子忽左忽右地滑动,在五彩斑斓的丝线上穿梭跳跃。手工织这样一匹绸子需要一个月时间。这一个月当中,贤龙不唱歌、不串门、不去集市,凭着废寝忘食的劲头儿,他连续不断地将心中的画面织出来。就算天光渐暗,他也能只靠手上的摸索, 明白经线上的颜色是否错位,图案的对称性是否圆满呈现。
那是一个人的美学史诗。他不能掺杂别人的意愿,不能有一丝敷衍马虎。所有的感触都是那么低微孤独又绚烂莫名。织成的绸子像抽象名画一样妩媚又深沉,将做成姑娘们的长裙,成为世间最美的风景……。他把绝活传给了阿女、有俊……
贤龙丝厂的丝绸远近闻名,顺庆府的丝绸商慕名而来,除买他的丝绸外,还要买他的绝活,价钱要多少就给多少,这贤龙不到两年,就翻了几倍的生意……真是:
春风竞放花千树,栽桑育、农家富。黎氏养蚕丝织布。
腊冬祭祀,来春腌种,收蚁蚕床宿。
茧儿白雪黄金缕,笑妇盈盈喜心腹。
设计缎绸全自举,绣图织画,名闻千里,富贵蒸蒸誉。
——《西湖路》
却说黎贤龙的丝绸厂越办越兴旺,远近绸商络绎不绝,引起了地方大大小小官员的嫉妒,最为恶毒的是官匪同道、叛难四起,众所周知,升钟区区长杜直廷、升钟区副团总傅文生、还有贤龙的拜把子袍哥掌门人、升钟区团练练总何尚文等,这些大官员通过变通的方式,给小官员增加了许多额外收入,这些收入往往被笼统地称为陋规,处于半合法地位,其数额常常是他们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按理,这些官员们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,但人是不知满足的动物,更何况是乱世之道,约束人心与行为的道德伦理,往往会被及时行乐的欲望所击溃。当“千里做官只为财”、“纱帽下面无穷汉”之类的理念成为官场上下奉行的人生准则时,恐怕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吏治也会束手无策。
民国官员们的黑色收入,除了历朝历代都免不了的下级向上级打点,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国家款项这种普遍性贪腐外,还有一些见诸正史和笔记的向民间直接捞钱的方式,堪称从蚊子腹内刳油,令人叹为观止。他们的贪腐除了直接从他们掌控的国家资源中“化公为私”、国家资源中侵吞,更为残酷的是通过种种方法,从老百姓身上巧取豪夺。这些官员为了从老百姓那里攫取钱财,其手段之下作,心肠之毒辣,名目之荒谬,都让人大开眼界。
按民国规定,商户都有向政府提供各种物品的义务。当然,商户向政府供货,政府也必须付费。具体做法是,一个地方的商户,按规模分为各种等级,或一年一轮,或一月一轮,轮番充任当行买办——替国家采购。在今天,这是一项很有油水的差事,不过现在的商户无不将其视为畏途。
首先是需要通过当行买办采购物资的政府各部门,几乎都采取先由当行买办按政府提供的清单购买交付,以后再结账的方式——但所谓的结账,运气好的商户,拖上三五年, 或许会得到一半的货款;运气不好的话,就可能成为一笔坏账,自掏腰包替政府买单。其次,更令商户头痛的是,即便你一开始就不准备把货款收回来,事情也没这么简单——送交政府的物资,官员们还得进行一番装模作样的验收。一旦没有行贿,再上等的商品也会被判定为“不中程”,即不合格。一旦判为不合格,商品原物退回还是其次,重要的是, 商户轻则会遭一顿暴打,重则被扔进大牢。
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之下,一旦不幸轮值出任当行买办,也就离家破人亡不远了。为此,贤龙的丝厂办的火红,第一、二年未必被官府看上眼,后来被官府发现后认为大有油水之捞。区长杜直廷亲自在厂里督管,几乎一半的丝绸被他们盘剥,自己的丝厂还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,幸好那里面贤龙还有个帮他说话的人何尚文,这何尚文表面上看起来是拜把子兄弟,尽管贤龙秘密私送了不少的丝绸,暗地里也和他们贯通一气,敲骨吸髓的盘剥对他的伤害巨大……
副团总傅文生得到贤龙的好处不多,唆使升钟黑帮头子杜彪在丝厂处处使坏。黑帮头子杜彪是当地的地痞、便称霸一方,为害相邻,成为升钟的土匪。由于杜彪作恶多端,被升钟团总何尚文派兵将其擒获,后欲斩首,被副团总傅文生得到贿赂后,关押了几天悄悄放了,杜彪感恩于傅文生,称傅文生是他的再生父母,这次他两密谋,成功后杜彪全利奉送。
哪知回龙又出了个黎攀龙、黎有坤、黎飞龙等人,暗地里成立了自己的袍哥组织,将附近的热血青年收拢……他们敢与当时的官府对抗。由于他们在皂角、思依活动,被群众称为梁山好汉,这次从升钟区保卫团分队长杜彦波秘密传来消息:黑帮头子杜彪某月某日要劫黎贤龙的丝厂,那攀龙、有坤那能坐视不管?他们几人背着黑枪,蒙面潜伏在大溪口拱桥两侧,专等杜彪的队伍……
忽然远处一阵阵的马蹄声,似乎是有千军万马赶过来一般。丝厂里的工人们都大惊, 有人忽然说是不是匪徒来了。听到这句话,所有人都惊慌起来,最后都静静的看着。
“没事的,大家先别慌,先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贤龙说道。其实贤龙心中也没底,不过贤龙还是抱着一种想法:是不是升钟又来人找我,他们一个是保卫团中队长伏蕴山, 一个是区长赵昌荣,绝对可以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要是其他的官员,他们只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以表示给我点惊喜。
可是,如果真的是土匪,就我这三脚猫的功夫,哪能摆平,更别说是一队人马了。 大家焦急的向村口走去,口中都在念叨着老天保佑之类的话,他们最怕的就是土匪,抢东西还是小事,要是出人命可就大事了。大凡土匪进村,一定是一阵烧杀,每个人心中都很紧张,这也是必然的,这贤龙自己心中也紧张,特别是他还承担着要保护自己厂里工人的重任。
“不好了,真的是土匪啊。”跑在最前面的小伙子突然叫了出来。
就在此刻,土匪们也和丝厂里的工人相遇了,丝厂里几十个人瞬间就被他们包围了。他们都拿着大刀斧头,吼吼叫叫耀武扬威,他们穿得花花绿绿的,确实不像是好人。
“相信工人们,我们见面了,不知道你们的主人还在不在啊。要是不在的话,麻烦接济我们一下,兄弟们在忍饥挨饿很久了,实在没有办法,这才向黎贤龙求助。”
说话的是一个骑着黑鬃大马的高大男子,此人面色偏黑,一双眼睛很是有神,声音也很粗,整体给人的感觉很是霸气。他说话的方式倒是挺彬彬有礼的,不过看他这阵容,不像是有礼,到更像是一种挑衅。
工人们听了他的话,都愣了一下,然后就是面面相觑,最后向那个家伙求饶,让他别伤害大家贤龙的父亲清田出来求情,让土匪别伤害厂里的工人。
那家伙看着清田,突然哈哈的笑了,然后很有礼貌的说道:“哦,你是贤龙的父亲, 您老人家还健在啊?这厂有您的带领,一定富足了不少吧。实在是对不住了。不过幸好贤龙那家伙出现了,也算是您老的福气。今天贤龙不在,我们你们就得小心点了,要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,我这些小弟,可是不受我操控的!……”
“贤龙虽然不在,可是他的工人在,你休想乱来。”人群中不知道谁吼出这么一句, 把在厂里的贤龙吓了一跳。贤龙回头看看众人,发现前前后后的人似乎都在看着他。那个土匪头子似乎也注意到了众人的动向,目光向贤龙所在的这个方向扫来。
“哪个是贤龙啊,出来让大爷我瞧瞧,我看看这个贤龙是不是三头六臂。”土匪头子说道。
贤龙在土匪火辣辣的目光中缓缓走出来,说道:“我就是贤龙,我就是贤龙!”
土匪头子见了贤龙,忽然就愣了一下,然后缓缓的冒出一句:“哦?原来是你,想不到你居然还是……?”
贤龙心中疑惑:他的口气似乎是见过我的,可是我对于他一点印象都没有,难道是因 为我失忆的原因么?
“你是谁?难道你认识我?”贤龙问道。
那家伙哼了一声,说道:“也算是有点认识吧。那一次我们抢劫陈家沟见过你。” 土匪头子哈哈一笑,说道:“其实也不算抢劫,就是去找点乐子,那次我们不什么也没有抢走嘛。哦对了,就是带走了两个美人,最后还是被你们给追回去了。说起来我还听得一些传言,说土匪杜彪把这两个美人带回去做了夫人,是吧?”
贤龙道:“今天来这里要想干什么?”
“我高兴来这里,我也乐意来这里,我想干什么,你管得着吗?”
贤龙此刻倒是不觉得害怕他,既然他来了,没非是想我那几匹丝绸罢了,我怕或者不怕,结局都是一样的。
“有什么话快说,说完快走。”贤龙说道。
土匪头子杜彪哼了一声,看看众人,说道:“好。爽快。我不相信你不使点本事,而且上次我们也是看你的面子才没有强行对村子抢劫。不过这一次就难说了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,一是我们将厂子里的人全部杀光,然后再把你女人和财物带走。二是你自动跟我们走,我可以答应不伤害厂里工人一根毛发,但你厂里的一切财物都带走?”
“有这好事?土匪进村简直就是强盗?”贤龙大声呵斥。
“土匪?别说那么难听,我们就是来求助的。不过现在看来你们厂也不大富裕,恰巧遇到你的夫人,所以顺便想请她去坐坐,虽然兄弟们饥渴难耐,可是会好好招待她的。” 杜彪哈哈笑着说道。
听了杜彪的话,工人们都议论纷纷,清田拉住贤龙,说道:“你能和他们去,他们都是没有人性的人。”
贤龙说道:“如果他真答应不伤害乡亲们,我和他走一趟又何妨。”转头对土匪头子说道:“好,我和你们走,不过你要说话算话,不准伤害他们。”
“好,只要你答应和我们走,我就不伤害他们,并保证以后都不会伤害他们。”他说道。
“好,一言为定。”
土匪们进了丝绸厂,见啥抢啥,抢走了上好的丝绸好几十匹,还砸坏了机具……
贤龙瞪了杜彪一眼,回头对工人们说道:“我没事的,大家不用担心,从今天起,你们暂时回家躲一躲,等我回来……”
“不行啊,我们怎么能让你这样跟他们去了。”
“对啊,这怎么可以。”
……
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一些担心的话,可是贤龙去意已决,只能让他们多保重。
在看着贤龙离开的一刻,发现工人们的眼睛湿润了,而且个个都呆呆的跪在地上,贤龙的父母、妻子阿女、孩子们都乱成一团,号声大哭,……
可是,没有办法,贤龙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护住他们,大家颓然的跪在地上,幽幽的说道:“你一定要平安无事,你一定会平安无事。”
在强敌面前,就算与他抗争,也是于事无补的,贤龙已经尽力了,任何事情尽力就行,没有必要你死我活的,最终两败俱伤就不好了。
土匪头子杜彪走了几步,把马头一转,对着众匪道:“我们把晚饭吃了走!好不好?” 众匪齐声道:“好!好!!”匪徒们下了马,立即擒鸡逮羊,闹得贤龙丝厂一片狼藉……
匪徒们吃了晚饭,押着贤龙,托上劫财,缓缓出发了……
且说有坤在大巴溪桥头的树林子等候土匪的到来,这个梁山好汉的袍哥组织有十几个彪悍,领头的就是贤龙的义子黎有坤,他很会带兵打仗,他根据土匪的惯例,土匪劫了财一般在晚上行走,夜晚少人出门,运送劫财不被人发现,特别是帮副团总傅文生,更应该隐蔽。他总结出“击尾不击头,击饱不击饿”的策略。土匪行动时,走在前面的都是不要命的悍匪,最好不要与其硬碰,设法拦腰攻击,先打战斗力差的土匪,引起土匪惊慌,容易将其击溃;轻装的土匪都似下山的饿狼,很难对付,而抢掠过后,他们兜里有钱,身上有包裹,人人无心恋战,就能轻松打败他们,夺下钱财和“肉票”,这地方甚好,只要土匪上了桥,两头一夹攻,他们谁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马,枪声一响,就会弃物而逃……靠着这些特殊的策略……
夜幕降临,月亮躲在云里。这时回龙堡就像一位巨人伏地而眠,在嘤嘤低唱的虫鸣中安详入睡。天上的星星,也疲倦地藏进乌云中困觉了。漆黑的山野,只有淅淅唰唰的雨点在微风中飘洒。
就在这个时候,“砰、砰、砰砰”的枪声即刻在大巴溪上空响起来了。
突如其来地短枪声,有坤的袍哥队都为之一振,他们议论说:“咋搞的嘛,战斗还没有开始,就响开了枪声?”
“糟糕了!敌人发现我们了。”飞龙和攀龙紧张对视。
“大家不要慌,这是土匪打黑枪,我们看看动静,再定夺吧。”有坤示意大家稳定情绪。
枪声响后,一切又平静下来。
“大家作好战斗准备!” 不一会儿,隐隐见马队上了桥,前面有攀龙和飞龙,后面有有坤。
“砰、砰……”前后一枪。
顿时,匪徒一片混乱,捞衣扎裤,挥枪舞棒,乱成了一锅粥。
黑夜的战斗对方在暗处,匪徒在明处,有坤的袍哥队只用了两枪,吓得匪首杜彪屁滚尿流,前后夹攻,阵脚迷乱,只有丢了一切,个个单身跳桥逃跑。
这次保守战术,双方人员没有伤亡。土匪摸不清情况,又是帮人劫财,送了命划不着, 枪一响就弃财而逃。所以没大动作了。有坤他们收拾了残局,见到了贤龙。
贤龙不知所为,惊讶的问: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,好久不见,很是想念!”
“干爹!我们回家再说。”
来到贤龙家,见家人及工人们还在流泪。“都快别哭了,土匪打跑了,贤龙回来了, 攀龙、有坤、飞龙……大家在一起了,今天要特别高兴诺”!清田安慰大家,自己也是赶紧的擦去了高兴的泪水。
“阿女,今天我亲自下厨,为义子、三弟,还有众兄弟搭救了我,我做一餐谢酒宴。” 贤龙拉着阿女的手说道。
“不,你去陪他们,有坤好久没来我家,还有你三弟……他们都想要我亲自做的饭菜了,这个面子要给啊。”阿女吃味的说道。
“多年不见,你可都还好吗?”贤龙温柔的问着有坤,有坤把参加袍哥为掩护,暗地里加入了武装革命的队伍,他们正准备积蓄力量,准备推翻升钟伪政府,发动一次武装暴动……有坤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的干爹贤龙。
贤龙大惊:“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!敢于官府作对,怕杀头吗?”
有坤道:“现在官匪同道、叛难四起,农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,国家灾难深重,解放人类要靠共产党……”黎有坤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理论,一时半会儿也不懂,贤龙只知道有坤、攀龙他们是杀富济贫、仗义疏财,为老百姓博施济众的侠士。
攀龙道:“大哥,你就参加我们的队伍吧!我们的帮主很欣赏你的为人,欣赏你的才华,你在渝州大闹禅林阳雀寺谁不知晓……”
贤龙道:“我参加事小,这屋大小几口人又怎样安排,我可以暗送情报,或暗地里为你们做点事是可以的,我是加入了何尚文的袍哥,他是团总,会给我面子的,再说,这丝厂是他二伯何国玉的,天不亮我就去何国玉家,把情况说给他,看他怎样处理……我只说是一伙蒙面人来劫财,遇巧碰上了这群土匪,我是在他们混乱中逃出来的……”
“你们吃了饭,把几匹丝绸托上,骑上马到思依去,神不知鬼不觉得无人知晓……官府也拿你们无办法……”贤龙道。“我们要抓紧点,说不定这些土匪仗着副团总傅文生, 天不亮定来找干爹的麻烦”有坤着急的说。幸好饭早就好了,他们草率的吃了点饭,收拾后,贤龙送他们出了门,安排了厂里的事宜,并吩咐如此如此,离开了家。
却说黑帮头子杜彪在黑夜里不知所措,只好逃命要紧,跳下桥不顾其溪水深浅,狼狈地向前跑着,衣服也因摔了跟头的缘故,显得那么破烂,但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,向前 跑,向前跑,一定要离开!中了子弹就没命了,渐渐的,他们跑不动了,只能疾步走着,脸色极其苍白,远处,传来了那追杀他们的人的声音,意识渐渐模糊,似乎,这一次,像是 自找的……
回到升钟区公所,那杜彪平时欺负人威风凛凛,现在是丑态百出。他敲着傅文生的房门,轻声地叫道:“傅团总,是我呀!傅团总,是我呀!……”这傅文生倒是听出了杜彪的声音,以为是叫他“收货” ,开门一看,见他全身水淋淋的惨样儿,知道是出了事了, 傅文生很是生气的问:“你这是怎么那?”杜彪哭丧着脸:“我们到了丝厂,装了绸缎及一切财物,带上贤龙,走到大巴溪桥上,从桥的两侧出现了不少的人马,真枪实弹两侧围堵我们,幸喜我们跳桥跑得快,不然,我们会全军覆灭。”“哪有这回事?撒谎你也不应该在我面前装模作样!”傅文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真,真的呀!不信,问他们……” 杜彪的几个狗腿子也跟上来,“是!是,我们差点送了命……”傅文生看到这些蠢蛋,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“那贤龙呢!”“不知去向,准时同伙的!”杜彪道。傅文生追问:“你们认识他们吗?”大家哑口无言,摇着头:“黑夜里哪知道是谁?”
“你几个全把事情搞杂了!叫你们蒙面偷偷的抢劫,你们大张旗鼓,都明了你们的身份,那贤龙是我们团总何义普(实名何尚文)拜把子的袍哥弟子,要是他知道,准没你们的命,而且,这丝绸厂还是团总二伯父大名鼎鼎三县十八场团正何国玉的,他要是找侄儿何义普打官司,你们能脱得了干系吗?你们最好的办法,连夜全部到深山里躲一段时间, 一年半载等风声平静了在露面,这样,才能保全你们的性命……”
杜彪听了,立即瘫痪在地,还是那几个喽啰扶着他走出了区公所大门。傅文生为了灭口,暗派他的手下,在八庙场处决了他们……
再说贤龙把事由的经过告诉了何国玉,何国玉天不亮找到了侄儿何尚文,把此事一说, 立即通令捉拿杜彪等人,通令一发出,有人报告说,八庙场发现了这几个人的尸首,具验证,却信,才把这事了结了。
贤龙遭此大劫,再不敢开丝绸厂了,有地主何尚礼大片土地无人耕种,劝其贤龙弃厂不如种地,“你丝绸厂虽盈利甚多,但风险大,各种税费加上官府层层敲诈勒索,你又盈利几何,不如种我的地,交租任你交多少我就收多少,你那榨房嘴几间茅房实在无法住人,搬迁到我何家湾,给你一个小院,房租全免……”
贤龙与妻子阿女商量,阿女也同意。第二年,全家搬迁到何家湾,住上了大瓦房式的东小院,租了何尚礼的二十多亩田地。不用说,丝厂里的工人全放了,只有幺娃和孬狗跟着贤龙种庄稼…… 闲时,贤龙做点盐和土烟生意,有时在家织点丝绸,在附近场镇贩卖, 倒也觉得轻松多了。真是:
设计缎绸全自举,绣图织画,富贵蒸誉。
赃官嫉妒,爱财心黑,借寇行禄。袭抢绸玉。
半途来夜遇神怒。惊吓滚桥溪,狼狈又恐怖。
只愿恩人护,人算命运,终是绝路。
——贺熙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