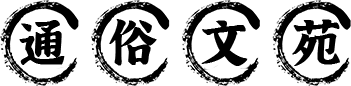第二十二回 贞倩女有心试情郎 花烛夜慧智辨新娘
词曰:
欲试情郎恋爱深,传音耗、礼相君。燕娇倚楚隔承恩,乍得见、两消魂。匆匆草草难留恋,三番去、定玄音。 假欢露雨与婚存,烈恋贵、终成姻。
再说华国在宋涛内厅吃完酒,叫人送在东书院歇宿,虽也有些酒意,却心下喜欢,全不觉醉。
华国因坐在床上,塌伏着枕头儿细想。道:“若没有可意之人,纵红成群,绿作队, 日夕相亲,却也无用。今既遇了此天生的尤物,且莫说无心相遇,信乎有缘﹔即使赤绳不系,玉镜难归,也要去展一番昆仑之妙手,以见吾钟情之不苟,便死也甘心。况宋老夫妻爱我不啻亲生,才入室,坐席尚未暖,早急呼妹妹以拜哥哥,略不避嫌疑,则此中径路, 岂不留一线。即宋氏小姐相见时,羞缩固所不免,然羞缩中别有将迎也。非一味不近人情, 或者展转反侧中,尚可少致殷勤耳。我之初意,虽蒙宋老苦苦相留,然非我四海求凰之本念,尚不欲久淹留于此。今既文君咫尺,再仆仆天涯,则非算矣。只得聊居子舍,长望东墙,再看机缘,以为进止。”想到快心,遂不觉沉沉睡去。正是:
蓝桥莫道无寻处,且喜天台有路通。
若肯沿溪苦求觅,桃花流水在其中。
到了次日,华国一觉醒来,早已红日照于东窗之上。恐怕亲谊疏冷,忙忙梳洗了,即 整衣,竟入内室来问安。宋涛夫妻一向孤独惯了,定省之礼,久已不望。忽见华国象亲儿 子的一般,走进来问安,不禁满心欢喜。因留他坐了,说道:“你实实是我家子侄,原该 以伯侄称呼,现竟是父子。今既相逢,我留你在此,这名分必先正了,然后便于称呼。” 华国听了,朗朗答应:“然先君生前友情,孩儿相见茫茫者,苦于不知也,今既剖明,忘 二大人之思为不义,似乎不可。望二大人仍置孩儿子膝下,则大人与先君当日一番友谊,不为虚哄一时也。”
宋涛夫妻听了,大喜不胜道:“我二人虽久矣甘心无子,然无子终不若有一子点缀目 前之为快。今见不夜,我不敢执前苦强者,恐立身扬名以显亲别有志耳。”华国道:“此 固大人成全孩儿孝亲之厚道,但孩儿想来,此事原两不相伤。二大人欲孩儿认义者,不过 欲孩儿在膝下应子舍之故事耳,非图孩儿异日拾金紫以增荣也。况孩儿不肖,未必便能上 达,即有寸进,仍归之先君,则名报先君于终天,而身侍二大人于朝夕,名实两全,或亦 未为不可也。不识二大人以为何如?”
宋涛听了,愈加欢喜道:“妙论,妙论,分别的快畅。竟以父子称呼,只不改姓便了。” 因叫许多家人仆妇,俱来拜见黎公子。因分付道:“这黎公子,今已结义我为父、夫人为母、小姐为兄妹,以后只称大相公,不可作外人看待。”众家人仆妇拜见过,俱领命散去。正是:
昨日还为陌路人,今朝忽尔一家亲。
相逢只要机缘巧,谁是谁非莫认真。
华国自在宋家认了父子,使出入无人禁止,虽住在东院,以读书为名,却一心只思量着宋氏小姐,要再见一面。料想小姐不肯出来,自家又没本事开口求见,只借着问安为名,朝夕间走到夫人室内来,希图偶遇。不期住了月余,安过数十次,次次皆蒙夫人留茶,留点心,留着说闲话,他东张西望,只不见小姐的影儿。不独小姐不见,连前番小姐的侍妾彩云影儿也不见,心下十分惊怪,又不敢问人,惟闷闷而已。
你道为何不见?原来小姐住的这拂云楼,正在夫人的卧房东首,因夫人的卧房墙高屋大,紧紧遮住,故看不见。若要进去,只要从夫人卧房后一个小小的双扇门儿入去,方才走得到小姐楼上。小姐一向原也到夫人房里来,问候父母之安,因夫人爱惜她,怕她朝夕间,拘拘的走来走去辛苦,故回了她不许来。惟到初一、十五日,宋涛与夫人到佛楼上烧香拜佛,方许小姐就近问候。故此夫人卧房中也来得稀少,惟有事要见,有话要说,方才走来。若是无事,便只在拂云楼上看书做诗耍子,并看园中花卉,及赏玩各种古董而已, 绝不轻易为人窥见。华国那里晓得这些缘故,只道是有意避他,故私心揣摹着急。不知人生大欲男女一般,纵是窈窕淑女,亦未有不虑摽梅失时,而愿见君子者。故宋氏小姐,自见华国之后,见华国少年清俊,儒雅风流,又似乎识窍多情,也未免默默动心。虽相见时不敢久留,辞了归阁,然心窝中已落了一片情丝,东西缥渺,却又无因无依,不敢认真。因此坐在拂云楼上,焚香啜茗,只觉比往日无聊。一日看诗,忽看见: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 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二句,忽然有触,一时高兴,遂拈出下句来作题目,赋了一首七言律诗道:
乌衣巷口不容潜,王谢堂前正卷帘。
低掠向人全不避,高飞入幕了无嫌。
弄情疑话来年旧,寻路喜窥今日檐。
栖息但愁巢破损,落花飞絮又重添。
宋氏小姐做完了诗,自看了数遍,自觉得意,惜无人赏识,因将锦笺录出,竟拿到夫人房里来,要寻父亲观看。不期父亲不在,房中只有夫人,夫人看见女儿手中拿着一幅诗笺,欣欣而来,因说道:“今日想是我儿又得了佳句,要寻父亲看了?”小姐道:“正是此意。不知父亲那里去了?”夫人道:“你父亲今早才吃了早饭,就被相好的一辈老友拉到玉虚庵看梅花去了。”小姐听见,便将诗笺放在靠窗的桌上,因与母亲闲话。
不期华国在东书院坐得无聊,又放不下小姐,遂不禁又信步走到夫人房里来,那里敢指望撞见小姐。不料才跨入房门,早看见小姐与夫人坐在里面说话。这番喜出望外,那里还避嫌疑,忙整整衣襟,上前与小姐施礼。小姐突然看见,回避不及,未免慌张。夫人因笑说道:“华国哥自家人,我儿那里避得许多。”小姐无奈,只得走远一步,敛衽答礼。见毕,华国因说道:“愚兄前已蒙贤妹推父母之恩,广手足之爱,持以同气,故敢造次唐突,非有他也。”小姐未及答,夫人早代说道:“你妹子从未见人,见人就要腼腆,非避兄也。”
华国一面说话,一面偷眼看那小姐。今日随常打扮,越显得妩媚娇羞,别是一种,竟看痴了。又不敢赞美一词,只得宛转说道:“前闻父亲盛称贤妹佳句甚多,不知可肯惠赐一观,以饱馋眼?”小姐道:“香奁雏语,何敢当才子大观。”夫人因接说:“我儿,你方才做的甚么诗,要寻父亲改削。父亲既不在家,何不就请哥哥替你改削改削也好。”小姐道:“改削固好,出丑岂不羞人。”因诗笺放在窗前桌上,便要移身去取来藏过。不料华国心明眼快,见小姐要移身,晓得桌上这幅笺纸就是他的诗稿,忙两步走到桌边,先取在手中,说道:“这想就是贤妹的珠玉了。”
小姐见诗笺已落华国之手,便不好上前去取。只得说道:“涂鸦之丑,万望见还。” 华国拿便拿了,还只认作是笼中娇鸟,彷佛人言而已,不期展开一看,尚未及细阅诗中之句,早看见蝇头小楷,写得如美女簪花,十分秀美,先吃一惊。再细看诗题,却是“赋得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”。先掩卷暗想道:“此题有情有态,却又无影无形,到也难于下笔,且看他怎生生发。”及看了起句,早已欣欣动色,再看到中联,再看到结句,直惊得吐出舌来。因放下诗稿,复朝着宋氏小姐,深深一揖道:“原来贤妹是千古中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女子,愚兄虽接芳香,然芳香之佳处尚未梦见。分日若非有幸,得览佳章,不几当面错过。望贤妹恕愚兄从前之肉眼,容洗心涤虑,重归命于香奁之下。”小姐道:“闺中孩语, 何敢称才?华国兄若过于奖夸,则使小妹抱惭无地矣。”
夫人见他兄妹二人你赞我谦,十分欢喜。因对华国说道:“你既说妹子诗好,必然深识诗中滋味,何不也做一首,与妹子看看,也显得你不是虚夸。”华国道:“母亲分付极是,本该如此,但恨此题实是枯淡,纵有妙境,俱被贤妹道尽,叫孩儿何处去再求警拔, 故惟袖手藏拙而已。”小姐听了道:“才人诗思,如泉涌霞蒸,安可思议。华国兄为此言,是笑小妹不足与言诗,故秘之也。”华国踌躇道:“既母亲有命,贤妹又如此见罪,只得要呈丑了。”彩云在旁听见黎公子应承做诗,忙凑趣走到夫人后房,取了笔砚出来,将墨磨浓,送在黎公子面前。华国因要和诗,正拿着小姐的原稿,三复细味,忽见彩云但送笔砚,并没诗笺,遂一时大胆竟在小姐原稿的笺后,题和了一首。题完,也不顾夫人,竟双手要亲手送与小姐道:“以鸦配凤,乞贤妹勿哂。”小姐看见,忙叫彩云接了来。展开一看,只见满纸龙蛇飞动,早已不同,再细细看去,只见写的是:
步原韵奉和宋氏仙史贤妹“赋得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”
经年不见宛龙潜,今日乘时重入帘。
他主我宾俱莫问,非亲即故又何嫌。
高飞欲傍拂云栋,低舞思依浣古檐。
只恐呢喃惊好梦,新愁旧恨为依添。
愚兄华国拜识
小姐看了一遍,又看一遍,见拂云浣古等句拖泥带水,词外有情,不胜惊叹道:“这方是大才子凌云之笔,小妹向来无知自负,今见大巫,应知羞而为之搁笔矣。”华国道: “贤妹仙才,非愚兄尘凡笔墨所能彷佛万一。这也无可奈何,但愚兄爱才有如性命,今既见贤妹阆苑仙才,琼宫佳句,岂不视性命为尤轻!是以得楚望蜀,更有无厌之请,望贤妹慨然倾珠玉之秘籍,以饱愚兄之饿眼,则知己深思,又出亲情之外矣。”小姐道:“小妹涂鸦笔墨,不过一时游戏。有何佳句,敢存笥箧,非敢匿瑕,实无残沈以博华国兄之笑。”华国听见小姐推说没有,不觉默然无语。彩云在旁,看见小姐力回,扫了黎公子之兴,因接说道:“大相公要看小姐的诗词,何必向小姐取讨?小姐纵有,也不肯轻易付与大相公, 恐怕大相公笑她卖才。大相公要看不难,只消到万卉园中,芍药亭、沁心堂、浣古轩,各处影壁上,都有小姐题情咏景的诗词,只怕公子还看她不了。”
华国听了方大喜,因对夫人说道:“孩儿自蒙父亲母亲留在膝下,有若亲生,指望孩 儿成名。终日坐在书房中苦读,竟不知万卉园中,有这许多景致。不但不知景致,连万卉 园,也不晓得在那里。今日母亲同孩儿贤妹,正闲在这里,何不趁此领孩儿去看看?”夫 人道:“正是呀,你来了这些时,果然还不曾认得。我今日无事,正好领你去走走。”遂 要小姐同去。小姐道:“孩儿今日绣工未完,不得同行,乞母亲哥哥见谅。”遂领着彩云 望后室去了。
此时华国见夫人肯同他到园中去,已是欢喜,忽又听见要小姐同去,更十分快活。正 打点到了园中,借花木风景好与小姐调笑送情,忽听见小姐说出不肯同去,一片热心早冷了一半。又不好强要小姐同去,只得生擦擦硬着心肠,让小姐走了。夫人遂带了几个丫鬟侍妾,引着华国,开了小角门,往园中而入。华国入到园中,果然好一座相府的花园,只见:
金谷风流去已遥,辋川诗酒记前朝。
此中水秀山还秀,到处莺娇燕也娇。
草木丛丛皆锦绣,亭台座座是琼瑶。
若非宿具神仙骨,坐卧其中福怎消?
华国到了园中,四下观看,虽沁心堂、浣古轩各处,皆摆列着珍奇古玩,触目琳琅, 名人古画,无不出奇,华国俱不留心去看他,只捡宋氏小姐亲笔的题咏,细细的玩诵。玩诵到得意之处,不禁眉宇间皆有喜色。因暗暗想道:“小姐一个雏年女子,貌已绝伦,又何若是之多才,真不愧才貌兼全的佳人矣。我华国今日何福,而得能面承色笑,亲炙佳章, 信有缘也。”想到此处,早呆了半晌。忽听见夫人说话,方才惊转神情。听见夫人说道: “此处乃你父亲藏珍玩之处,并不容人到此,只你妹子时常在此吟哦弄笔。”
华国听了,暗暗思量道:“小姐既时常到此,则她的卧房,必有一条径路与此相通。” 遂走下阶头,只推游赏,却悄悄找寻。到了芍药台,芙蓉架,转过了荷花亭,又上假山, 周围看这园中的景致。忽望北看去,只见一带碧瓦红窗,一字儿五间大楼,垂着珠帘。华国暗想道:“这五间大楼,想是小姐的卧房了。何不趁今日也过看看?”遂下了假山,往雪洞里穿过去,又上了白石栏杆的一条小桥,桥下水中,红色金鱼在水面上啖水儿,见桥上有人影摇动,这些金色俱跳跃而来。华国看见,甚觉奇异,只不知是何缘故。华国过了小桥,再欲前去,却被一带青墙隔断。华国见去不得,便疑这楼房是园外别人家了,遂取路而回,正撞着夫人身边的小丫鬟红菊走来。说道:“夫人请大相公回去,叫我来寻。” 华国遂跟着红菊走回。华国正要问她些说话,不期夫人早已自走来,说道:“我怕你路径不熟,故来领你。”华国又行到小桥,扶着栏杆往下看鱼。因问道:“孩儿方才在此走,为何这些鱼俱望我身影争跳?竟有个游鱼啖影之意。”夫人笑说道:“因你妹子闲了,时常到此喂养,今见人影,只说喂它,故来讨食。”华国听了大喜,暗暗点头道:“原来鱼 知人意。”夫人忙叫人去取了许多糕饼馒头,往下丢去,果然这些金鱼都来争食。华国见了,甚是欢喜。看了一会,同着夫人一齐出园。回到房中,夫人又留他同吃了夜饭,方叫 他归书房歇宿。真是:
佳人只要心儿俏,俏便思量到。从头直算到收梢,不许情长情短忽情消。
一时任性颠还倒,那怕旁人笑。有人点破夜还朝,方知玄霜捣尽是蓝桥。
——虞美人
话说华国自从游园之后,又在夫人房里吃了夜饭,回到书房,坐着细想:“今日得遇小姐,又得见小姐之诗,又凑着夫人之巧,命我和了一首,得入小姐之目,真侥幸也。” 心下十分快活。只可恨小姐卖乖,不肯同去游园,又可恨园中径路不熟,不曾寻见小姐的拂云楼在那里。想了半晌,忽又想道:我今日见园中各壁上的诗题,如《好鸟还春》,如《莺啼修竹》,如《飞花落舞筵》,如《片云何意傍琴台》,皆是触景寓情之作,为何当此早春,忽赋此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之句,殊无谓也。莫非以我之来无因,而又相亲相近若有因,遂寓意于此题么?若果如此,则小姐之俏心,未尝不为我华国不夜而踌躇也。况诗中之“全不避”、“了无嫌”,分明刺我之眼馋脸涎也。”想来想去,想的快活,方才就寝,真是:
穿通骨髓无非想,钻透心窝只有思。
想去思来思想极,美人肝胆尽皆知。
到了次日,华国起来,恐怕错看了小姐题诗之意,因将小姐的原诗默记了出来,写在 一幅笺纸上,又细细观看。越看越觉小姐命题的深意原有所属,暗暗欢喜道:小姐只一诗题,也不等闲虚拈。不知他那俏心儿,具有许多灵慧?我华国若不参透他一二分,岂不令 小姐笑我是个蠢汉?幸喜我昨日的和诗,还依稀彷佛,不十分相背。故小姐几回吟赏,尚 似无鄙薄之心。或者由此而再致一诗一词,以邀其青盼,亦未可知也。但我想小姐少师之 女,贵重若此﹔天生丽质,窃宛若此﹔彤管有炜,多才若此。莫说小姐端庄正静,不肯为薄劣书生而动念,即使感触春怀,亦不过笔墨中微露一丝之爱慕,如昨日之诗题是也。安 能于邂逅间,即眉目勾挑,而慨然许可,以自媒自嫁哉,万无是理也!况我华国居此已数月矣,仅获一见再见而已。且相见非严父之前,即慈母之后,又侍儿林立,却从无处以叙寒温。若欲将针引线,必铁杵成针而后可。我华国此时,粗心浮气,即望玄霜捣成,是自弃也。况我奉母命而来,原为求婚,若不遇可求之人,尚可谢责。今既见宋氏小姐绝代之 人,而不知极力苦求,岂不上违母命,而下失本心哉?为今之计,惟有安心于此,长望明河,设或无缘,有死而已。但恨出门时约得限期甚近,恐母亲悬念,于心不安。况我居于此,无多役遣,只八卦一仆足矣。莫若打发七娃归去报知,以慰慈母之倚闾。思算定了,遂写了一封家书,并取些盘缠付与七娃,叫他回去报知。宋涛与夫人晓得了,因也写下一 封书,又备了几种礼物,附去问候。七娃俱领了。收拾在行李中,拜别而去。正是:
书去缘思母,身留冀得妻。
母妻两相合,不问已家齐。
华国自打发了七娃回家报信,遂安心在花丛中作蜂蝶,寻香觅蕊,且按下不题。
却说宋氏小姐自见华国的和诗,和得笔墨有气,语句入情,未免三分爱慕,又加上七 分怜才,因暗暗忖度道:少年读书贵介子弟,无不翩翩。然翩翩是风流韵度,不堕入裘马豪华,方微有可取。我故于华国公子,不敢以白眼相看。今又和诗若此,实系可儿。才貌虽美,但不知性情何如?性不定,则易更于一旦,情不深,则难托以终身,须细细的历试之。使花柳如风雨之不迷,然后裸从于琴瑟未晚也。若溪头一面,即赠皖纱,不独才非韫玉,美失藏娇,而官门楣,不几扫地乎?
自胸中存了一个持正之心,而面上便不露一痕容悦之像。转是彩云侍儿忍耐不住,屡 屡向小姐说道:“小姐今年二十,年已及笄。虽是相门人家千金小姐,又美貌多才,自应贵重,不轻许人,然亦未有不嫁者。老爷夫人虽未尝不为小姐择婿,却东家辞去,西家不允,这还说是女婿看得不中意。我看这华国公子行藏举止,实是一个少年的风流才子。既无心撞着,信有天缘。况又是冠家子侄,门户相当,就该招做东床,以完小姐终身之事。为何又结义做儿子,转以兄妹称呼,不知是何主意?老爷夫人既没主意,小姐须要自家拿 出主意来,早作红丝之系,却作不得儿女之态,误了终身大事。若错过了华国公子这样的才郎,再期求一个如黎公子的才郎,便难了。”
宋氏小姐见彩云一口直说出肝胆肺腑之言,略不忌避,心下以为相合,甚是喜他。便不隐讳,亦吐心说道:“此事老爷也不是没主意,无心择婿。我想他留于子舍者,东床之渐也。若轻轻的一口认真,倘有不宜,则悔之晚矣。就是我初见面时,也还无意,后见其信笔和诗,才情跃跃纸上,亦未免动心。但婚姻大事,其中情节,变换甚多,不可不虑,所以蓄于心而有待。”
彩云道:“佳人才子,恰恰相逢,你贪我爱,谅无不合。不知小姐更有何虑?小姐若 不以彩云为外人,何不一一说明,使我心中也不气闷?”小姐见彩云之问话问得投机,知心事瞒他不得,遂将疑他少年情不常,始终有变,要历试他一番之意,细细说明。彩云听了,沉吟半晌道:“小姐所虑固然不差。但我看华国公子之为人十分志诚,似不消虑得。然小姐要试他一试,自是小心过慎,却也无碍。但不知小姐要试他那几端?”
小姐道:“少年人不患其无情,而患其情不耐久。初见面既亲且热,恨不得一霎时便偷香窃玉。若久无顾盼,则意懒心隳,而热者冷矣,亲者疏矣。此等乍欢乍喜之人,妾所不取。故若亲若近,冷冷疏疏,以试黎郎。情又贵乎专注,若见花而喜,见柳即移,此流荡轻薄之徒,我所最恶。故欲情人掷果,以试黎郎。情又贵乎隐显若一,室中之展转反侧, 不殊抮大道之秣马秣驹,则其人君子,其念至诚。有如当前则甜言蜜语,若亲若昵,背地则如弃如遗,不瞅不睬,此虚浮两截之人,更所深鄙。故欲悄悄冥冥潜潜等等,以试黎郎。况他如此类者甚多,故不得不过于珍重,实非不近人情而推聋作哑。”
彩云道:“我只认小姐遇此才人,全不动念,故叫我着急。谁知小姐有此一片深心, 蓄而不露。今蒙小姐心腹相待,委曲说明,我为小姐的一片私心方才放下。但只是还有一 说……”小姐道:“更有何说?”彩云道:“我想小姐藏于内室,黎公子下榻于外厢,多时取巧,方得一面?又不朝夕接谈,小姐就要试他,却也体察不能如意。莫若待彩云帮着小姐,在其中探取,则真真假假,其情立见矣。”小姐听了大喜道:“如此更妙。”二人 说得投机,你也倾心,我也吐胆,彼此不胜快活。正是:
定是有羞红两颊,断非无恨蹙双眉。
万般遮盖千般掩,不说旁人那得知。
却说彩云担当了要帮小姐历试华国公子有情无情,便时常走到夫人房里来,打听乎黎公子的行事。一日,打听得黎公子已差七娃回家报知黎夫人,说他在此结义为子,还要多住些时,未必便还。随即悄悄通知小姐道:“黎公子既差人回去,则自不思量回去可知矣。我想他一个富贵公子,不思量回去,而情愿留此独居,以甘寂寞,意必有所图也。若细细揣度他之所图,非图小姐而又谁图哉?既图小姐,而小姐又似有意,又似无意,又不吞, 又不吐,有何可图?既欲图之,岂一朝一夕之事,图之若无坚忍之心,则其倦可立而待。我看黎公子去者去,留者留,似乎有誓守蓝桥之意。此亦其情耐久之一征,小姐不可不知。” 小姐道:“你想的论的未尝不是。但留此是今日之情,未必便定情终留于异日。我所以要姑待而试之。”
二人正说不了,忽见红霞走来,笑嘻嘻对小姐说道:“黎公子可惜这等样一个标致人儿,原来是个呆子。”小姐因问道:“你怎生见得?”红霞道:“不是我也不知道,只因方才夫人取了一盘荔枝,叫我送与黎公子去吃。我送到书房门外,听见黎公子在内说话。我只认是有甚朋友在内,不敢轻易进去。因在窗缝里一张,那里有甚朋友,他独自一人穿得衣冠齐齐整整,却对着东边照壁上一幅诗笺,吟哦一句,即赞一声‘好!’就深深的作一个揖道:‘谢淑人大教了。’再吟哦一句,即又赞一声‘妙!’又深深作一个揖,道: ‘蒙淑人垂情了!’我偷张不得一霎,早已对着壁诗,作过十数个揖了。及我推门进去, 他只吟哦他的诗句,竟象不曾看见我的一般。小姐你道呆也不呆?你道好笑也不好笑?” 小姐道:“如今却怎么样了?”红霞道:“我送荔枝与他,再三说夫人之话,他只点点头, 努努嘴,叫我放下,也不做一声。及我出来了,依旧又在那里吟哦礼拜,实实是个呆子。” 小姐道:“你可知道他吟哦的是甚么诗句?”红霞道:“这个我却不知道。”
这边红霞正长长短短告诉小姐,不期彩云有心,在旁听见,不等红霞说完,早悄悄的走下楼来,忙闪到东书院来窃听。听见黎公子还在房里,对着诗壁跪一回,拜一回,称赞好诗不绝口。彩云是个急性人,不耐烦偷窥,便推开房门,走了进去,问黎公子,道:“大相公,你在这里与那个施礼,对谁人说话?”华国看见彩云,知他是小姐贴身人,甚是欢喜。因微笑答应道:“我自有人施礼说话,却一时对你说不得。”彩云道:“既有人,在那里?”华国因指着壁上的诗笺道:“这不是?”彩云道:“这是一首诗,怎么算得人?” 华国道:“诗中有性有情,有声有色,字字皆是慧心,句句无非妙想。况字句之外,又别自含蓄无穷,怎算不得人?”彩云道:“既要算人,却端的是个甚人?”华国道:“观之艳丽,是个佳人﹔读之芳香,是个美人﹔细昧之而幽闲正静,又是个淑人。此等人,莫说眼前稀少,就求之千古之中,也似乎不可多得。故我华国于其规箴讽刺处,感之为益友﹔ 于其提撕点醒处,敬之为明师﹔于其绸缪眷恋处,又直恩爱之若好逑之夫妇。你若问其人为何如,则其人可想而知也。”彩云笑道:“据大相公说来,只觉有模有样。若据我彩云看来,终是无影无形。不过是胡思乱想,怎当得实事?大相公既是这等贪才好色,将无作有,以虚为实,我这地方,今虽非昔,而浣纱之遗风未散,捧心之故态尚存,何不寻他几个来,解解饥渴?也免得见神见鬼,惹人讥笑。”
华国听了,因长叹一声道:“这些事怎可与人言?就与人言,人也不能知道。我华国若是等闲的蛾眉粉黛可以解得饥渴,也不千山万水来到此地了。也只为香奁少彩,彤管无花,故检遍春风而自甘孤处。”彩云道:“大相公既是这等看人不上眼,请问壁上这首诗,实是何人做的,却又这般敬重他?”华国道:“这个做诗的人,若说来你到认得,但不便说出。若直直说出了,倘那人闻知,岂不道我轻薄?”彩云道:“这人既说我认得,又说不敢轻薄他,莫非就说的是小姐?莫非这首诗,就是前日小姐所做的赋体诗?”华国听见彩云竟一口猜着他的哑谜,不禁欣然惊讶道:“原来彩云姐也是个慧心女子,失敬,失敬。” 彩云因又说道:“大相公既是这般敬重我家小姐,何不直直对老爷夫人说明,要求小姐为婚?况老爷夫人又极是爱大相公的,自然一说便允。何故晦而不言,转在背地里自言自语,可谓用心于无用之地矣。莫说老爷夫人小姐,不知大相公如此至诚想望﹔就连我彩云,不是偶然撞见问明,也不知道,却有何益?”
华国见彩云说的话,句句皆道着了他的心事,以为遇了知己,便忘了尔我,竟扯彩云坐下,将一肚皮没处诉的愁苦,俱细细对她说道:“我非不知老爷夫人爱我,我非不知小姐的婚姻,原该明求。但为人也须自揣,你家老爷一个黄阁门楣,岂容青衿溷辱?小姐一位上苑甜桃,焉肯下嫁酸丁?开口不独徒然,恐并子舍一席,亦犯忌讳而不容久居矣。我筹之至熟,故万不得已而隐忍以待。虽不能欢如鱼水,尚可借雁影排连以冀一窥色笑。倘三生有幸,一念感通,又生出机缘,亦未可知也。此我苦情也。彩云姐既具慧心,又有心怜我,万望指一妙径,终身不忘。”
彩云道:“大相公这些话,自大相公口中说来,似乎句句有理﹔若听到我彩云耳朵里,想一想,则甚是不通。”华国道:“怎见得不通?”彩云道:“老爷的事,我捉摸不定,姑慢讲。且将小姐的事,与你论一论。大相公既认定小姐是千古中不可多得之才美女子, 我想从来惟才识才,小姐既是才美女子,则焉有不识大相公是千古中不可多得之才美男子之理?若识大相公是才美男子,则今日之青衿,异日之金紫也,又焉有侍贵而鄙薄酸丁之理?此大相公之过虑也。这话只好在我面前说,若使小姐闻知,必怪大相公以俗情相待,非知己也。”华国听了,又惊又喜道:“彩云姐好细心,怎直想到此处?想得甚是有理, 果是我之过虑。但事已至此,却将奈何?”
彩云道:“明明之事,有甚奈何?大相公胸中既有了小姐,则小姐心上,又未必没有大相公。今所差者,只为隔着个内外,不能对面细细讲明耳。然大相公在此,是结义为子,又不是过客,小姐此时,又不急于嫁人。这段婚姻,既不明求,便须暗求。急求若虑不妥,缓求自当万全。那怕没有成就的日子?大相公不要心慌,但须打点些巧妙的诗才,以备小姐不时拈索,不至出丑,便万万无事了。”华国笑道:“这个却拿不稳。”又笑了一回, 就忙忙去了。 正是:
自事自知,各有各说。
情理多端,如何能决?
话说彩云问明了黎公子的心事,就忙忙归到拂云楼,说与小姐知道。不期小姐早在那里寻她,一见了彩云,就问道:“我刚与红霞说得几句话,怎就三不知不见了你,你到那里去了这半晌?”彩云看见红霞此时已不在面前,因对小姐说道:“我听见红霞说得黎公子可笑,我不信有此事,因偷偷走了去看。”小姐道:“看得如何,果有此事么?”彩云 道:“事便果是有的,但说是呆子,我看却不是呆,转是正经。说他可笑,我看来不是可笑,转是可敬。”遂将黎公子并自己两人说的话,细细说了一遍与小姐听。小姐听了,不禁欣然道:“原来他拜的就是我的赋体诗。他前日看了,就满口称扬,我还道他是当面虚扬,谁知他背地里也如此珍重。若说他不是真心,这首诗我却原做的得意。况他和诗的针芥,恰恰又与我原诗相投。此中韵味,说不得不是芝兰。但说恐我不肯下嫁酸丁,这便看得我太浅了。”
彩云道:“这话他一说,我就班驳他过了。他也自悔误言,连连谢过。”小姐道:“据你说来,他的爱慕于我,专注于我,已见一斑。他的情之耐久,与情之不移,亦已见之行事,不消再虑矣。但我想来,他的百种多情,万般爱慕,总还是一时之事。且藏之于心,慢慢看去,再作区处。”彩云道:“慢看只听凭小姐,但看到底,包管必无破绽,那时方知我彩云的眼睛识人不错。”自此二人在深闺中,朝思暮算,未尝少息。正是:
苦极涓涓方泪下,愁多蹙蹙故眉颦。
破瓜之子遭闲磕,只为心中有了人。
却说华国自被彩云揣说出小姐不鄙薄他,这段婚姻到底要成,就不禁满心欢喜,便朝夕殷殷勤勤,到夫人处问安,指望再遇小姐,扳谈几句话儿。谁知走了月余,也不见个影儿。
宋夫人看出华国的心思,便到小姐房间,正好红霞、彩云在场,宋夫人问起小姐道:“华国有爱慕小姐之意,你如何看待?”宋氏小姐道:“黎公子胸中既有了小姐,则吾心上又未必没有黎公?看母亲意下如何?”于是红霞、彩云试探黎公子的事告诉了宋夫人。
晚上,宋涛回到家里,夫人把黎公子与小姐的事告诉了宋涛,宋涛道:“华国公子初来认义子欲后为女婿耳,这时间长了,相恋已久,托月老谋婚。不过,且试他一试。”
第二天,宋涛传华国至内堂,当面提出小姐的婚事,准备择日完婚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,一天华国随着岳父母二人走至拂云楼下,早见彩云巧梳云鬓,薄着罗衣,与宋氏小姐一样装束。手捧着一个小小的锦袱,立于楼厅之右,也不趋迎,也不退避。华国见了,便举手要请她相见。彩云早朗朗的说道:“相见当以礼,今尚不知宜用何礼,暂屈公子少缓,且请公子先看了小姐之手书,再定名分相见何如?”因将所捧的小锦袱放在当中一张桌上,打开了,取出宋氏小姐的手札来,叫一个侍妾送与华国。彩云乃说道:“是 假是真,公子请看。”华国接在手中,还有三分疑惑,及定睛一看,早看见书面上写着: “薄命落难妾宋氏小姐谨致书寄上黎公亲启密览”二十二个小楷,美如簪花,认得是小姐的亲笔,方敛容滴泪道:“原来宋氏小姐,当此倥偬之际,果相念不忘,尚留香翰以致殷勤,此何等之恩,何等之情,义当拜受。”因将书仍放在桌上,跪下去再拜。
宋老看见,忙搀住道:“这也不消了。”华国拜完起来,见书面上有“密览”二字, 遂将书轻轻拆开,走出楼外阶下去细看。只见上写道:
妾闻婚姻之礼,一朝终身。今既遭殃,死生已判。若论妄为郎而死,死更何言?一念及生者之恩, 死难瞑目。想郎失妾而生,生应多恨﹔若不辜死者之托,生又何惭?亿自郎吞声别去,满望吐气锦归,不道谗入九重,祸从天降。自应形消一旦,恨入地中,此皆郎之缘悭,妾之命薄。今生已矣,再结他生,夫复谁尤?但恐妾之一死,漠漠无知,窃恐黎郎多情多义,怜妾之受无辜,痛妾之遭荼毒,甘守孤单,则妾泉下之魂,岂能安乎?再三苦思,万不得已,而恳父母收彩云为义女,欲以代妾而奉箕帚。有如黎郎情不耐长,义难经久,以玉堂金马,而别牵绣幕红丝,则彩云易散,原不相妨。倘黎郎情深义重,生死不移, 始终若一,则妾一线未了之盟,愿托彩云而再续。若肯怜贱妾之死骨而推恩,则望勿以彩云之下体而见弃。代桃以李,是妾痴肠。落月存星,望黎郎刮目。不识黎郎能如妾愿否?倘肯念旧日之鸠鹊巢,仍肯坦别来之金紫腹,则老父老母之半子,有所托矣。老父老母之半子既有托,则贱妾之衔结,定当有日。哀苦咽心, 言不尽意,乞黎郎垂谅,不宣。
华国读了一遍,早泪流满面。及再读一回,忽不禁哀哀而哭道:“小姐呀,小姐呀! 你不忍弃我华国之盟,甘心一死,则孤贞苦节,已自不磨。怎又看破我终身不娶,则知己之感,更自难忘。这还说是人情,怎么又虑及我之宗嗣危亡,怎么又请人代替,使我义不能辞!小姐呀,小姐呀,你之心胆,亦已倾吐尽矣!”因执书沉想道:我若全拒而不从, 则负小姐之美意﹔我若一一而顺从,则我华国假公济私,将何以报答小姐?”又思量了半晌,忽自说道:“我如今有主意了。”遂将书笼入袖中,竟走至楼下。
此时彩云见华国持书痛哭,知华国已领会小姐之意,不怕他不来求我,便先上楼去了。宋老见华国看完书入来,因问道:“贤婿看小女这封书,果是真么?”华国道:“小姐这封书,言言皆洒泪,字字有血痕。不独是真,而一片曲曲苦心,尽皆呕出矣。有谁能假?” 宋老道:“既是这等,则小女续盟之议,不知黎公以为何如?”华国道:“宋氏小姐既拚一死矣,身死则节着而名香矣,她何必虑?然犹于思百虑,念我华国如此,则言言金玉也。华国人非土木,焉敢不从?”宋老道:“黎公既已俯从,便当选个黄道吉日,要请明结花烛矣。”华国道:“明结花烛,乃令爱小姐之命,当敬从之,以尽小姐念我之心。然花烛之后,尚有从而未必尽从之微意,聊以表我华国不忘小姐之私,亦须请出二小姐来,细细面言明方好。”
宋老听了,因又着红霞去请,回复道:“二小姐说,黎公若不以大小姐之言为重,不愿结花烛则已﹔既不忘大小姐,而许结花烛,且请结过花烛以完大小姐之情案。若花烛之后,而黎公别有所言,则其事不在大小姐,而在二小姐矣。”华国听了,点头道是,遂不敢复请矣。宋老与何夫人见婚盟已定,满心欢喜。遂同华国出到后厅,忙忙吩咐家人去打点结花烛之事。 正是:
妙算已争先一着,巧谋偏占后三分。
其中默默机锋对,说与旁人都不闻。
宋老见华国允从花烛,便着人选吉日,并打点诸事具已齐备。
华国到了正日,暗自想道:“彩云婢作夫人,若坐在他家,草草成婚,岂不道我轻薄?轻薄他不打紧,若论到轻薄他,即是轻薄了小姐,则此罪我华国当不起了。”正好七娃从老家带来珍奇异宝,检选了数种,叫人先鼓乐喧天的送到宋老府中,以为聘礼。然后自穿了婚服,坐了显轿,一路灯火,吹吹打打而来,人人到宋老府中去就亲,好不兴头。
到了府门,见黎公子到了,媒人忙叫众侍妾簇拥出二小姐来,同拜天地,同拜父母, 又夫妻交拜。拜毕,然后拥入拂云楼上去,同饮合卺之卮。外面宋老自与媒人同饮喜酒不题。
且说华国与彩云二人到了楼上,此时彩云已揭去盖头,四目相视,华国忙上前,又是一揖道:“我华国向日为小姐抱病时,多蒙贤卿委曲周旋,得见小姐,以活余生,到今衔感,未敢去心。不料别来遭变,月缺花残,只道今生已矣,不意又蒙小姐苦心,巧借贤卿以续前盟。真可谓恩外之恩,爱中之爱矣。今又蒙不辜小姐之托,而殷懃作天台之待,华国虽草木,亦感春恩。但在此花烛洞房,而小姐芳魂不知何处,生死关心,早已死灰槁木。若欲吹灯含笑,云雨交欢,实有所不忍,欲求贤卿相谅。”说罢,凄凄咽咽,若不胜情。
彩云自受了小姐之托,虽说为公,而一片私心,则未尝不想着偎偎倚倚,而窃黎公之恩爱。今情牵义绊,事已到手,忽见黎公子此话,渐渐远了,未免惊疑。因笑嘻嘻答道: “黎公此话就说差了。花是花,叶是叶,原要看得分明。事是事,心是心,不可认做一样。贱妾今日之事,虽是续先姐之盟,然先姐自是一人,贱妾又是一人。黎公既不忘先姐,却也当思量怎生发付贱妾。不忍是心,花烛是事。黎公昔日之心,既不忍负,则今日之花烛,又可虚度耶?黎公风流人也,对妾纵不生怜,难道身坐此香温玉软中,竟忍心而不一相慰藉耶?”华国道:“贤卿美情,固难发付,花烛良宵,固难虚度,但恨我华国一片欢情, 已被小姐之冤恨沉沉销磨尽矣,岂复知人间还有风流乐事?芳卿纵是春风,恐亦不能活予枯木。”
彩云复笑道:“阳台云雨,一笑自生,但患襄王不入梦耳。黎公岂能倦而不寝耶?且请少尽一卮,以速睡魔,周旋合卺。”因命侍儿捧箸以进。黎公接卮在手,才吃得一口, 忽突睁两眼,看看彩云,大声叹息道:“天地耶?鬼神耶?何人欲之溺人如此耶?我华国之慕小姐,几不能生﹔小姐为我华国,已甘一死。恩如此,爱如此,自应生生世世为交颈鸳,为连理树。奈何遗骨未埋,啼痕尚在,早坐此花烛之下,而对芳卿之欢容笑口,饮合卺卮耶?使狗彘有知,岂食吾余?何不速傍烟销,早随灯灭,也免得出名教之丑,而辱我宋氏小姐也!”哀声未绝,早涕泗滂沱,而东顾西盼,欲寻死路。
彩云见华国情义激烈,因暗忖道:“此事只宜缓图,不可急取。急则有变,缓则终须到手。”因急上前再三宽慰道:“黎公不必认真,适才之言乃贱妾以试黎公之心耳。黎公以千秋才子,而独定情于先姐﹔先姐以绝代佳人,而一心誓守状元,此贱妾之深知也。贱妾何人,岂不自揣,焉敢昧心蒙面,而横据鹊巢,妾冀黎公之分爱?不过奉先姐之遗命, 欲以窃黎公半子之名分,以奉两亲耳。至于贱妾,娇非金屋,未免有玷玉堂,吐之弃之, 悉听黎公,贱妾何敢要求?”华国听了,方才破涕说道:“贤卿若能怜念我华国至此,则贤卿不独是华国之知己,竟是保余我华国名节之恩人矣。愿借此花烛之光,请与贤卿愿做闺中小妹,则情义两全矣。”彩云道:“此非黎公之创论,‘琴瑟友之’,古人已先见之于诗矣。”华国听了,不觉失笑。二人说得投机,因再烧银烛,重饮合欢,直尽醉方止。彩云因命侍妾另设一榻,请黎公对寝。正是:
情不贪淫何损义,义能婉转岂伤情。
漫言世事难周到,情义相安名教成。
到了次日,二人起来,华国梳洗,彩云整妆,说说笑笑,宛然与夫妻无疑。
却说宋夫人闲中,偶问及彩云,华国结亲情义何如,彩云方将华国苦守小姐之义,万万不肯交欢之事,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听了,虽感激其不忘小姐,却恐怕彩云之婚又做了空帐,只得又细细与宋老商量。宋老听了,因惊怪道:“此事甚是不妥,彩云既不曾与他粘体,两头俱虚,实实没些把臂。他若推辞,反掌之事。”夫人道:“若是如此,却将奈何?”宋老道:“我如今有个主意了。”夫人道:“你有甚么主意?”宋老道:“我想鸠鹊争巢,利于先入。黎婿既与彩云明偕花烛,名分已正,其余闺阁之私,不必管他。我总闲在此,何不拼些工夫,竟将彩云送至蜀中,交付黎亲母做媳妇。既做了媳妇,黎婿归来,纵不欢喜,却也不能又生别议。况黎婿守义,谅不别娶。归来与二女朝朝暮暮,雨待云停,或者一时高兴,也不可知。若到此时,大女所托之事,岂不借此完了?”夫人听了,喜道:“如此甚妙。但只愁你年老,恐辛苦去不得。”宋老道:“水有舟,旱有车马,或亦不妨。” 夫人道:“既如此,事不宜迟,须作速行之。”宋老留下何夫人,背着华国,带上佣人与小姐、彩云打点入蜀。
却说宋老同了彩云、小姐并侍从,望四川而来,喜得一路平平安安,不日到了阆中升钟,寻了寓处住下,随命家人到升钟黎家坝去报知。家人寻到了,因说道:“我是湖北武当十堰宋老爷家的家人,有事要禀见黎夫人。”门上人见说是宋小姐家里人,便不敢停留,即同他到厅来见黎夫人。宋家人见了黎夫人,忙磕头禀道:“小人是湖北武当十堰宋老爷家家人,黎公子与家老爷是翁婿。故家老爷亲送小姐到此,拜见老夫人。今已到在寓处, 故差小人来报知。”黎夫人香君及黎府上下人等出来迎接。
宋老已有佣人报知,喜个不了,巴不得立刻就来相见。及轿马到了,一刻也不停留, 就同小姐、彩云上轿而来。
大家吃完喜酒,就请宋老到东边厅里住下。彩云小姐遂请入后房,与宋氏小姐同居, 就絮絮聒聒,说了一夜。说来说去,总说的是黎公子有情有义,不忘小姐之事。宋氏小姐听了,不胜感激。因暗暗想道:“当日一见,就知黎郎是个至诚君子,故赋诗寓意,而愿托终身。今果能死生不变,我宋氏亦可谓之识人矣。但既见了我的书,肯与彩云续盟,为何又坐怀不乱?只这一句话,尚有三分可疑。”也不说破,故大家在闺中作乐,以待黎公归来,再作道理。
过了月余,宋老就要辞归,宋氏小姐苦苦留住,那里肯放。又恐母亲在家悬望,又打发家人先去报喜。宋老只得住下。又过不得月余,忽有报到,黎公子和书童七娃、八卦回来了。
宋氏小姐闻知,因暗暗对黎夫人说道:“黎公归时,望婆婆且莫说出媳妇在此,须这般这般,试他一试,方见他一片真心”黎夫人听了道:“有理,有理,我依你行。”遂一一吩咐了家下人。
华国迎接到家,先拜了祖先,然后拜见父亲母亲道:“孩儿只为贪名,冬温夏清之礼, 与晨昏定省之仪皆失,望父亲母亲恕孩儿之罪。”父母亲道:“出身事主,何在朝夕。” 华国又请哥嫂对拜。拜毕,黎夫人因又说道:“湖北亲家,远远送了媳妇来,实是一团美意。现住在东厅,你可快去拜见谢他。”华国道:“宋岳父待孩儿之心,实是天高地厚。但不该送此媳妇来,这媳妇之事,却非孩儿所愿,却怎生区处?”黎夫人道:“既来之, 则安之,有话且拜见过再说。”
华国遂到东厅,来拜见宋老道:“小婿因归心急,有失趋侍,少答劬劳,即当晨昏子舍,怎反劳岳父大人跋涉远道,叫小婿于心何安?”宋老道:“儿女情深,不来则事不了, 故劳而不倦,黎公宜念之。”话未说完,彩云早也出来见了。见毕,华国因说道:“事有根因,我华国与贤卿所续之盟,是为宋非为黎也。贤卿为何远迢迢到此?”彩云因答道: “事难逆料,黎公与贱妾所守之戒,是言死而非言生也,贱妾是以急忙忙而来。”
华国听了,一时摸不着头路。因是初见面,不好十分抢先,只得隐忍出来,又见母亲。 黎夫人因责备他道:“你当先初出门时,你原说要寻一个媳妇,归来侍奉我。后又说寻着了宋家小姐,幸不辱命。宋老又亲送女儿来与你做媳妇,自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美事,为何你反不悦?莫非你道我做母亲的福薄,受不起你夫妻之拜么?”华国道:“母亲不要错怪了孩儿,孩儿所说寻着了宋家小姐,是大女宋氏小姐,非二女彩云小姐也。”黎夫人道:“既是大小姐,为何宋亲家又送二小姐来?”华国道:“有个缘故,大小姐不幸遭变,为守孩儿之节死了,故岳父不欲寒此盟,又苦苦送二小姐来相续。”
黎夫人道:“续盟之意,宋亲家可曾与你说过?”华国道:“已说过了。”黎夫人道: “你可曾应承?”华国道:“孩儿原不欲应承,只因大小姐有遗书再三嘱托,孩儿不敢负她之情,故勉强应承了。”黎夫人道:“应承后可曾结亲?”华国道:“亲虽权宜结了, 孩儿因忘不得大小姐之义,却实实不曾同床。”黎夫人道:“你这就大差了。你虽属意大小姐,大小姐虽为你尽节,然今亦已死矣。你纵义不可忘,只合不忘于心,再没而守匹夫不娶小节之理。宋亲家以二小姐续盟,自是一团美意。你若必欲守义,就不该应承,就不该结亲﹔既已结亲,而又不与同床,你不负心固是矣,而此女则何辜?殊觉不情。况你在壮年,不遂家室,将何以报母命?大差,大差!快从母命,待我与你再结花烛。”华国道:“母亲之命,焉敢有违。但不必同床,却是孩儿报答宋氏小姐之一点痴念,万万不可回也。” 黎夫人笑一笑道:“我儿莫要说明,倘到其间,这点痴念,只怕又要回了,却将如何?” 华国说到伤心,不觉凄然欲哭道:“母亲,母亲,若要孩儿这点痴回时,除非宋氏小姐再世重生,方才可也”
黎夫人听了,又笑一笑道:“若是这等说,我要回你的痴念头便容易了。”华国也只说母亲取笑,也不放在心上。黎夫人果然叫人检了一个黄道吉日,满厅结彩铺毡,又命乐人鼓乐喧天,又命家人披红挂彩,又命礼生往来赞襄,十分丰盛热闹。到了黄昏,满厅上点得灯烛辉煌。礼生喝礼,先请了黎公新郎出来,然后一阵侍妾簇拥着珠冠霞帔宋老小姐出来,同拜天地,又同拜父亲母亲,又同拜泰山宋老。拜毕,然后笙箫鼓乐,迎入洞房。正是:
白面乌纱正少年,琼姿玉貌果天然。
若非种下风流福,安得牵成萝琵缘?
黎公子与小姐到了房中,虽是对面而坐,同饮合欢,却面前摆着两席酒,相隔甚远。席上的锭盛糖果,又高高堆起,遮得严严,新人虽揭去盖头,却缨络垂垂,挂了一面,那里看得分明。况华国心下已明知是彩云小姐,又低着头不甚去看,那里知道是谁。左右侍妾,送上合卺酒来,默饮了数杯,俱不说话。又坐了半晌,将有请入鸳帏之意,华国方开 口对着新人说道:“良宵花烛,前已结矣。合卺之卮,前已饮矣。今夕复举者,不过奉家慈之命,以尽贤卿远来之意。至于我华国感念令先姐之思义,死生不变,此贤卿所深知,不待今日言矣。分榻而寝,前已有定例,不待今日又讲矣。夜漏已下,请贤卿自便,我华国要与令先姐结梦中之花烛矣。疏冷之罪,统容荆请。”
说罢就要急走出房去。只见新人将双手分开面上的珠络,高声叫道:“黎郎,黎郎, 你看我是那个?你果真为我宋氏多情如此耶!你果真为我宋氏守盟如此耶!我宋氏女获此义夫,好侥幸耶!”华国突然听见宋氏小姐说话,吃了一惊,再定睛一看,认得果是宋氏小姐。这一喜非常,便不问是生是死,是真是假,忙走上前,一把抱定不放。道:“小姐呀,小姐呀!你撇得我华国好狠耶,你想得华国好苦耶!你今日在此,难道不曾死耶,你难道重生耶,莫非还是梦耶?快说个明白?”小姐道:“黎公不须惊疑,妻已死矣,幸得有救,重生在此。”华国道:“果是真么?”小姐道:“若不是真,小妹缘何在此?”华国方大喜道:“贤妹果重生,只怕我华国又要喜死耶?即遗书托令妹续盟这一段委曲深情, 也感激不尽。”
小姐道:“黎公既念妻之情而不忍违,又守妾之义而断不染,真古今钟情人所未有,叫我小妹如何不私心喜而生敬?”华国道:“此一举,在贤妹可以表情,在愚兄可以明心,俱得矣。只可怜令妹,碌碌为人,而徒享虚名,毫无实际,她一副娇羞热面,也不知受了我华国多少抢白﹔她一片恳款真心,我华国竟不曾领受他半分。今日得与夫人相见,而再一回思,殊觉不情,不能无罪。明日还求贤妹,率我去负荆以请。”宋氏小姐道:“这也不消了。舍妹前边的苦尽,后面自然甘来,何须性急?可趁此花烛,着人请来,当面讲明,使大家欢喜。”
侍妾才打帐去请,原来彩云此时正俏俏伏在房门外,听他二人说话,听到二人说他许多好处,再听见叫侍妾请他,不待请竟揭开房帏,笑嘻嘻走了入来,说道:“二新人幸喜相逢,我小妹也只得要三曹对案了。华国疑小姐的手书是假,今请问小姐是假不是假?姐姐疑黎公与妹子之花烛,未必无染,今请问黎公是有染是无染?”华国与宋氏小姐一齐笑说道:“手书固然是真,而续盟亦未尝假。从前虽说无染,而向后请将颜色染深些,以补不足,亦未为不可。二小姐何必这等着急?”彩云听了,也忍不住笑将起来。华国因命撤去套筵,重取芳樽美味,三人促膝而饮。细说从前许多情义,彼此快心。直饮到醉乡深处,方议定今宵巫峡行云,明夕阳台行雨,先送彩云到闺房,然后华国携宋氏小姐同入温柔, 以完满昔日之愿。正是:
人心乐处花疑笑,好事成时烛有光。
不识今宵鸳帐里,痴魂销出许多香。
到了次夜,宋氏小姐了无妒意,立逼黎郎与彩云践约。华国再三不允,后将彩云另嫁何尚坤,这是后话。正是:
记得闻香甘咽唾,常羞对美苦流涎。
今宵得做鸳鸯梦,这段风流岂羡仙。
华国闺中快乐,过了三朝,然后率媳妇,拜见婆婆。黎夫人见他们美美满满,如鱼水和谐,怎么不喜。又同拜见岳丈,宋老更是欣然。大家欢欢喜喜,倏忽过了半年。有诗赞曰:
恋爱长期经磨练,偎依伴侣何曾欢。
若非心有相安处,未免摇摇看意丹。
况是轻盈过燕燕,更加娇丽胜莺兰。
忧寻烛夜真娘献,坎坷多难总聚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