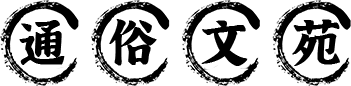第二十八回 入空门险遭毒僧丧命 弹棉褥走红江湖营生
词曰:
空门误入遭冥灭,又见僻山血。认识老妇诉何如,唯有福缘少女救难出。笑是金莲消国步,玉树明前赴。拜师弹褥喜明珠,由来倾国逢巧娶蓉芙。 ——虞美人
话说华国的次子林春二十岁,生得肌如雪晕,唇若朱涂,一个脸儿,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,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。他虽才学不精,但大智若愚,冰雪聪慧,心灵手巧。华国六十六岁,见他还未立业。有焦虑之心。一日,家制棉褥,林春购置弹弓一副,巧能制褥,华国见之,让他出外制褥营生。
一日,林春独自与四位经纪人同道往顺庆一带作制褥手工活,那四位是谁?一个姓何名通,升钟场何家山人;一个姓张名军,升钟场张家湾人;一个姓宋名显,保城场宋家坪人;一个姓杜名锡山,升钟场杜家湾人;四人里头,唯杜锡山家事凉薄些儿。那三位却也一个个殷足,带足了到顺庆做生意的资费,唯有林春只带了弹弓一副和随身穿戴。这几个同道,好不高兴,个个人材表表,气势昂昂,十分齐整。怎见得?有一词曰:
轻眉俊眼,舞拳腿步,衣雨风笠飘露。
欣然行走互帮衬,顺山路、攀险用武。
右悬包裹,右挎衣绣,习辗风尘乐苦。
那堪历履越溪流, 五人赴、竟前曲度。
——广寒秋
这班从人打扮出路光景,虽然是山村勇粗,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 人,第一是“老成”二字最为紧要。一举一动,俱要留心。进入西充边境,各家打开了银包,兑了多少银钱,放在皮囊里头,随身放少许零用铜钱,万防不测。一路上见的,只认是铜钱在衣内,那里晓得是银钱在里头。行到西充地方,离城尚有二十里。路上荒凉,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。抬头观看,望着一座大寺:
苍松虬结,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,插汉芙蓉;百道鸣泉,洒空珠玉。螭头高拱,上逼层霄;鸱吻分张, 下临无地。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,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。 寺门上有金字牌扁,名曰窦禅寺。
这几个整日劳顿,见了这么大寺院,心中欢喜。一齐缓步,进去游玩。但见稠阴夹道, 曲径纡回,旁边多少旧碑,七横八竖,碑上字迹模糊,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这窦禅寺踞于西充槐树场西南处,佛教圣地,山体独居,四周无任何遮挡,山势大奇特,风景秀丽, 该寺历史悠久,东汉永平年词,白窦禅师高僧圆寂后改“圭峰禅院”为“窦禅寺”。
正看之间,有小和尚疾忙进报。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,摆将出来。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,便鞠躬迎进。逐一位见礼看座。问了某姓某处,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。那几个随即问道:“师父法号?”那和尚道:“小僧贱号慧真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干,到荒寺经过?”众人道:“我们都是顺庆府做生意的。在此经过。见寺宇整齐,进来随喜。” 那和尚道:“失敬,失敬!家师远出,有失迎接,却怎生是好?”说了三言两语,走出来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。便走到门前观看。只见行李十分华丽,个个鲜衣大帽。眉头一蹙, 计上心来。暗暗地欢喜道:“这些行李,若谋了他的,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,他每在此逗留,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,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,再作区处。” 转身进来,就对众人道:“列位相公在上,小僧有一言相告,勿罪唐突。”众人道:“但说何妨。”和尚道:“说也奇怪,小僧昨夜得一奇梦,梦见天上大星,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,变了几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: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。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生意发旺,决不出五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,虽不敢屈留尊驾,但小僧得此佳梦,意欲暂留过宿。列位相公,若不弃嫌,过了一宿,应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蔌,怠慢列位相公,不要见罪。”众人听见说了生意发旺,决应在我们之中,欲待应承过宿。只有黎林春心中疑惑。密向其四同友道:“这样荒僻寺院,和尚外貌虽则殷勤,人心难测。他苦苦要留,必有缘故。”四同友道:“黎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四人,都是雄粗勇猛的, 还怕这几个乡村和尚。若黎兄行李万一他虞,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林春道:“前边只有二十里,便到歇宿所在。还该赶去,才是道理。”
却有何通与张军都是极高兴的朋友,心上只是要住宿。对林春道:“且莫说天色已晚, 赶不到场店。此去途中,尚有可虑。现成这样好僧房,受用一宵,明早起身,也不为误事。 若黎兄必要赶到槐树场,黎兄自请先行,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,黎林春声声要去。便向林春道:“相公,此处去十来里有飞虎岭,歹人极多。此时天色已晚, 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,不如小房过夜,明日早行,差得几时路程,却不安稳了多少。”林春被众友牵制不过,又见和尚十分好意;况且跟随的人,见寺里热茶热水,也懒得赶路。向主人道:“这师父说飞虎岭晚上难走,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林春见说得有理, 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拿进行李,明早起程。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。连忙备办酒席,吩咐道人,宰鸡杀鹅,烹鱼炮鳖,登时办起盛席来。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?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,件色鸡鹅等类,都养在家里,因此捉来便杀。不费工夫。佛殿旁边转过曲廊,却有一间精致客堂,摆下一桌筵席,下边列着一个陪桌,共是两席,十分齐整。慧真举杯安席。五同友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,张军开言道:“列位兄弟,必须行一酒令,才是有兴。”宋显道:“师父,这里可有色盆?” 和尚道:“有,有。”连唤道人取出色盆,斟着大杯,送第一位何通行令。何通也不推逊,吃酒便掷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,上口便干。原来这酒不比寻常,却是把酒来浸米,麯中又放些香料,用些热药,做来颜色浓酽,好像琥拍一般。上口甘香,吃了便觉神思昏迷,四肢痑软。这几个同友吃惯了歪酒,水般样的淡酒,药般样的苦酒,还有尿般样的臭酒,这晚吃了恁般浓酝,加倍放出意兴来。猜拳赌色,一杯复一杯,吃一个不住。那慧真和尚又叫小和尚都来劝酒,那四同友吃得泥烂。只有林春吃到中间,觉酒味香浓,心中渐渐昏迷。 暗道:“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!且是昏迷神思,其中决有缘故。”就地生出智着来,假做腹痛,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,却道:“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,必是多吃热酒,才可解散。如何倒不用酒?”一齐来劝。那和尚道:“黎相公,这酒是三年陈的,小僧辈置在床头,不敢轻用。今日特地开出来,奉敬相公。腹内作痛,必是寒气,连用十来大杯,自然解散。”黎林春看他殷勤劝酒,心上愈加疑惑,坚执不饮。众人道:“林春兄为何这般扫兴?我们是畅饮一番,不要负了师父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,只放林春不过。心上道:“他不肯吃酒,不知何故?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”又把大杯斟送。林春道:“实是吃不下了,多谢厚情。”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却说那些小和尚,接了这些行李,铺下铺盖。这些吃醉的同友,大家你称我颂,乱叫着某行长、某会长,东歪西倒,跌到房中,面也不洗,衣也不脱,爬上床磕头便睡,齁齁鼻息,响动如雷,吃是眼定口开,手痑脚软,做了一堆矬倒。
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,他便如何不受酒毒?他每吩咐小和尚,另藏着一把注子,色味虽同,酒力各别。间或客人答酒,只得呷下肚里,却又有解酒汤,在房里去吃了,不得昏迷。酒散归房,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,思量动手。慧真道: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,不可迟延。万一酒力散了,便难做事。”吩咐各持利刃,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,听了一番,思待进房中间,又有一个本地和尚,号曰文空,悄向慧真道:“这些谨慎了当,必须静等,要一一搅触一下,如未惊醒,方觉无事,才能动手,永无遗患。”慧真点头道: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,掇开房门,见头便割。这班酒透的人,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,一齐杀倒,血流遍地。其实堪伤!
却说那黎林春因是心中疑惑,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该绝,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。侧耳听着外边,只觉酒散之后,寂无人声。暗道:“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,收了这残盘剩饭, 必然聚吃一番,不然,也要收拾家伙,为何寂然无声?”又少顷,闻得窗外悄步,若有人声,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,只听得外厢连叫哎哟,又有模糊口声。又听得匹扑的跳响, 慌忙跳起道:“不好了,不好了!中了贼僧计也!”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,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,那里推得醒。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,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。推了几推,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。林春顾不得别人,事急计生,耸身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,猛力爬上,偷眼观看。只见也有和尚,也有俗人,一伙儿拥进房门,持着利刃,望颈便刺。林春见众人被杀,惊得心摇胆战,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,奋身一跳,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,又想后窗不曾闭得,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,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,满面流血,钻出棘丛,拔步便走。却是硬泥荒地。带跳而走,已有四五里之远。云昏地黑,阴风淅淅,不知是什么所在。却都是废冢荒丘。又转了二个弯角儿,却见一所人家,孤丁丁住着,板缝内尚有火光。林春想:“我已筋疲力尽,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息,只得哀求借宿,再作道理。”正是:
贫穷富贵本兄哥,恶吉全然未醒活。
毒手贼髡谋俊儒,提防那会命逃脱。
林春低声叩门,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妪,点灯开门。见了林春道:“夜深人静,为何叩门?”林春道:“昏夜叩门,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,只得求妈妈方便。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妪道:“老身孤寡,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,又无随从,不知来历, 决难从命!”林春暗道:事到其间,不得不以实情告他。便道:“妈妈在上,其实小生姓黎,是升钟回龙场人,到顺庆府买卖来此。被窦禅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狼心,把我四位同友都灌醉了,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,幸得逃生。”老妪道:“哎哟!阿弥陀佛!不信有这样事!”林春道:“你不信,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,跳出荆棘丛中,面都刺碎。”老妪睁睛看时,果然面皮都碎。对林春道:“相公果然遭难,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生意旺了,看顾老身,就有在里头了。”林春道:“极感妈妈厚情!自古道: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。我替你关了门,你自去睡。我就在此桌儿上假寐片时。一待天明,即便告别。”老妪道:“你自请稳便。那个门没事,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,难得贵公到来。常言道:贵人上宅,柴长三千,米长八百。我老身有一个姨娘,是卖酒的,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,替相公压惊,省得你又无铺盖,冷冰冰地睡下去。”
黎林春只道脱了大难,心中又惊又喜,谢道:“多承妈妈留宿,已感厚情!又承赐酒,何以图报?小生倘有财旺,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:“相公且宽坐片时,有外甥女奉陪。老身暂去就来。外甥女过来,见了相公。你且把门儿关着,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妪吩咐外甥女几句,随即提壶出门去了,不提。
却说那外甥女子把林春仔细端详,若有嗟叹之状。林春道:“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?”女子道:“年方十九岁。”林春道:“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?”女子道。“我看你堂堂容貌,表表姿材,受此大难,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聪敏睿智,看不出人情世故。”林春惊问道:“你为何说此几句,令我好生疑异?”女子道:“你只道我家舅母为何不肯留你借宿?”林春道:“孤寡人家,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: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,他又如何肯留起来?”林春道:“这是你舅母恻隐之心,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:“这叫做燕雀处堂,不知祸之将及。”
林春益发惊问道:“难道你舅母也待谋害我不成?我如今孤身无物,他又何所利于我?小姐,莫非道我伤弓之鸟,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?”女子道:“你知道我远房舅母家住居的房屋是哪个的房屋?营运的本钱是哪个的本钱?”林春道:“小姐说话好奇怪!这是你远房舅母家事,小生如何知道?”女子道:“妾姓文,名迎春,住槐树场文家嘴,我母亲叫文珍,父亲叫文家民,终年在民间弹花制褥,未曾在家,这几天我在舅母家帮她打杂, 舅父名叫文讯彩,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,也是窦禅寺慧真和尚的,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,我的舅哥文空是我舅父过继的儿子,舅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。幸不在家。 若要撞见相公,决不相饶。”林春想道:“方才众和尚行凶,内中也有俗人,一定是文空了。”便问道:“既是你舅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,如何又买酒请我?”女子道:“他那里真个去买酒。假此为名,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。你终须一死!我见你丰仪出众,决非凡品,故此对你说知。放你逃脱此难!”
林春吓得浑身冷汗,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:“你去了不打紧,我家舅母极是利害,她回来不见了你,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,教我怎生禁受?”林春道:“你若有心救我,只得吃这场责罚,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:“有计在此!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,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舅母,等她回来,只告诉她说你要把我强奸,绑缚在此。被我叫喊不过,也怕舅母归来,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,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怀中取出鸳鸯赋一支,赠与林春,并嘱咐:“回来时,到我文家嘴提亲!”又顺便把柜子里一小箱取出来,放在桌子上,倒了一杯药茶放在凳子上,道:“这正是和尚借我家舅母的本钱。若舅母问起,我自有言抵对;这药茶里面有慢性剧毒,你到一半留一半放在凳子上,”林春初不欲受,思量前路盘缠,尚无毫忽,只得受了,把小箱摔在地上。把杯子里的毒水倒了一半后放在凳子上,把这女子绑缚起来,心中暗道:“此女仁智兼全,救我性命,不可忘她大恩。不如与她定约,异日定娶她回去。”便向女子道:“小生黎林春,年二十岁,南部升钟人氏,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,意欲结为夫妇,后日娶你,决不食言。小姐意下如何?”女子道:“妾小名迎春,今年十九岁。若不弃微贱,永结葭莩,死且不恨。只是一件:我舅母通报寺僧,也是平昔受他恩惠,故尔不肯负她。请君日后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,君无留恋。”林春闻言一毕,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,回头一看,只见后边一队人众,持着火把,蜂拥而来。林春魂飞魄丧,好像失心风一般,望前乱跌,也不敢回头再看。真是:
寺院遇僧屠,逃跑姻缘谱。径向小棘湾,泥沾来晚呼。
借睡横波怒,才女情由吐。 惊胆唬心扑,设法龙凤福。
——醉公子
话分两头。单提那老妪打头,引众僧手持木棍在前,慧真随后,也有文空,通共有六七余人,气吽吽一直赶到老妪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相近,乱叫乱哭。老妪一进门来,不见了姓黎的;只见女子被缚,吓了一跳,道:“外甥女为何倒缚在那里?”女子哭道:“那人见舅母出去,竟要把我强奸,道我不从,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,只得奔去。 又转身进来翻箱倒柜。我回他没法,竟向箱中拿了甚么,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妪闻言,好像落汤鸡一般,口不能言。连忙拾起箱子查看,几锭银子全没了。叫道:“不好了!前借师父的本钱,反被他全掏摸去了。”众和尚不见林春,也没工夫逗留,连忙向外追赶。女子道:“你们不必惊恐,他已经喝了我的毒茶,天亮必死无疑。”众僧拾起杯子,果真有毒,才无戒心。他们到处寻了一阵,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,跌脚叹道:“打蛇不死,自遗其害。” 事已如此,真是喝了毒茶!也就放心。把杀死众尸,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, 原来多是铜钱在内。银子也有八九百两。把些来分与众和尚、众道人等。也分些与文空。人人欢喜,个个感激。又另把些送与老妪。一则买他的口,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。依旧作借。
却说那林春,脱身之后,黑地里走来走去,原只在一处地方,气力都尽。只得蹲在一个树林子里头。天色微明,向前又走,已到西充县。刚待进县,遇着一个老叟,连叫:“老侄,如何在此独步,没人随从?”
那老叟你道是谁?却就是林春的叔父,叫做黎昆明,一向在顺庆做生意,贩货回家, 在此劈面撞着了侄儿,真是一天之喜。林春正值穷途,撞见了自家的叔父,把窦禅寺受难根因,与老妪家脱身的缘故一一告诉。黎昆明十分惊唬!他叔父挽着林春的手,拖到饭店上吃了饭,林春为了不辜负四友同道之情,写了状子和他叔父一道来到顺庆府,见了顺庆知府李民圣的副官张宝,把四个同友受害本末,细细与知府说知。
那知府李民圣的副官张宝素有父亲华国交好。他们来到西充县衙,随着府县拘窦禅寺僧人到县。即将为首僧人慧真、觉空二人,极刑鞫问,招出杀害生意人何通、张军、宋显、 杜锡山。押赴后园,起尸相验。随将众僧拘禁。知府即时提请灭寺屠僧,立碑道旁,地方称快。
后林春回来,亲到废寺基址,作诗吊祭四位同友,不提。
却说那老妪原系和尚心腹,一闻寺灭僧屠,逃到文家嘴姑妹家避难。迎春心中暗道:“我若不告诉母亲和舅母,前日那林春从何寻问?”正在忧惶,只见一位老人走进门来,问道:“这里可是文家吗?”文珍道:“老身便是。”老叟道:“令爱可叫文迎春么?” 文珍道:“小女的名字,老人家如何晓得?”老叟道:“老夫是升钟黎家坝,我侄儿黎林春,在此经过,不意这里窦禅寺和尚忽起狼心,谋害同行四位生意人,侄儿幸脱此难。现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,又谢他赠了盘缠银几锭,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。”
老妪听了,吓呆了半晌,无言回答。那迎春窥见舅母情慌无措,扯她与她母亲到房中说道:“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,面若中秋之月,色如春晓之花,鬓若刀裁,眉如墨画, 面如桃瓣,目若秋波,是我心中的男子汉。孩儿惜他一命,只得赠了盘缠放他逃去,那毒茶是女儿设的套,认为他已毒死,稳住众僧不去征讨,彼时感激孩儿,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:‘舅母平昔受了寺僧恩惠,纵去报与寺僧知道,也是各不相负。你切不可怀恨。’ 他有言在先,你今日不须惊怕。林春就接女儿到黎家坝,也不会记恨舅母的。”迎春的母亲文珍道:“既如此,大嫂何必情慌无措?”
老妪不敢进见林春,女儿苦苦代舅母请罪,方得相见。老妪匍伏而前。林春扶起行礼,不提前事。这叫做:夫妻同是前生定,曾向蟠桃会里来。有诗为证:
春闱赴选遇强徒,解厄全凭女丈夫。
凡事必须留后着,他年方不悔当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