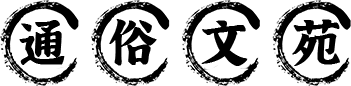第二十六回 信媒娘出走他乡女遭罪 误歧途逃难山寨郎遇缘
词曰:
自古人间,百家女面,绝不同颜。万派千支,同胞兄妹,相貌各兼。
案行真假伏潜,有道是、曲折搅玄。 认定姻缘,上天成眷,犯罪深渊。
——云淡秋空
话说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,盖因各父母所生,千支万派,那能勾一模一样的?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,同胞双生的儿子,道是相象得紧,毕竟仔细看来,自有些少不同去处。却又作怪,尽有途路各别、毫无干涉的人,蓦地有人生得一般无二、假充得真。孔子貌似阳虎以致匡人之围,周坚死替赵朔以解下宫之难,是贱人象了贵人,是个解不得的道理。
话说黎华国的长女春花。年方十六,生得如花似玉,美冠一方。父母勤俭,家道富有, 宝惜异常,娇养过度。凭媒说合,嫁与保宁府聚龙湾严松为妻。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。他要说了穷,石崇也无立锥之地。他要说了富,范丹也有万顷之财。正是:富贵随口定,美丑趁心生。再无一句实话的。那保宁府聚龙湾严氏虽是个旧姓人家,却是个破落户,家道艰难,外靠男子出外营生,内要女人亲操井臼,吃不得闲饭过日的了。这个严松虽是人物也有几分象样,已自弃儒为商。况且公婆甚是狠戾,动不动出口骂詈,毫没些好歹。春花父母误听媒人之言,道他是好人家,把一块心头的肉嫁了过来。少年夫妻过得就不恩爱,只是看了许多光景,心下好生不然,如常偷掩泪眼。严松晓得意思,把些好话偎她过日子。却早成亲两月,也未成同床,这严公哪里知道?严父就发作儿子道:“如此你贪我爱,夫妻相对,白白过世不成?如何不想去做生意?”严松无奈,与妻春花说了。次日严父就要儿子出外去了。春花独自一个,越越凄惺。况且是个娇美的女儿,新来的媳妇,摸头路不着,没个是处,终日闷闷过了。严父严母看见媳妇这般模样,时常急聒,骂道:“这婆娘想甚情人?害相思病了!”春花生来在父母身边如珠似玉,何曾听得这般声气?不敢回言,只得忍着气,背地哽哽咽咽,哭了一会罢了。一日,因春花起得迟了些个, 公婆朝饭要紧,粹地答应不迭。严公开口骂道:“这样好吃懒做的淫妇,睡到这等一同才起来!看这自由自在的模样,除非去做娼妓,倚门卖俏,掩哄子弟,方得这样快活象意。若要做人家,是这等不得!”春花听了,便道:“我是好人家儿女,便做道有些不是,直得如此作贱说我!”大哭一场,没分诉处。到得夜里睡不着,越思量越恼,道:“老无知! 这样说话,须是公道上去不得。我忍耐不过,且跑回家去告诉爹娘。明明与他执论,看这话是该说的不该说的!亦且借此为名,赖在家多住几时,也省了好些气恼。”算计定了。侵晨未及梳洗,将一个罗帕包裹扎了,一口气跑到嘉陵江渡口来。
只因此去,天气却早,虽是已有行动的了,人踪尚稀,渡口悄然。这地方有一个专一做坏事的光棍,名唤缪浪儿,绰号“雪里狼”,是个冻饿不怕专挑便宜的混儿。也是黎春花合当悔气。撞着他独自个江中乘了竹筏,未到渡口,望见了个花朵般后生妇人,来到岸边。又且头不梳裹,满面泪痕,晓得有些古怪。在筏上问道:“娘子要渡江么?”春花道:“正要过去。”缪浪儿道:“这等,上我筏来。”一口叫:“放仔细些!”一手去接她下来。上得筏,一篙撑开,撑到一个僻静去处,问道:“娘子,你是何等人家?独自一个要到那里去?”春花道:“我自要到黎家坝娘家去。你只送我到江一上岸,我自认得路,管我别管做甚?”缪浪儿道:“我看娘子头不梳,面不洗,泪眼汪汪,独身自走,必有跷蹊作怪的事。说得明白,才好渡你。”春花在水中央了,又且心里急要回去,只得把丈夫不在家了、如何受气的上项事,一头说,一头哭,告诉了一遍。缪浪儿听了,便心下一想, 转身道:“这等说,却渡你去不得。你起得没好意了,放你上岸,你或是逃去,或是寻死, 或是被别人拐了去,后来查出是我渡你的,我却替你吃没头官司。”春花道:“胡说!我自是娘家去,如何是逃去?若我寻死路,何不投水,却过了渡去自尽不成?我又认得娘家路,没得怕人拐我!”缪浪儿道:“却是信你不过,既要娘家去,我舍下甚近,你且上去我家中坐了。等我走去对你家说了,叫人来接收去,却不两边放心得下?”春花道:“如此也好。”正是女流之辈,无大见识,亦且一时无奈,拗他不过。还只道好心,随了他来。 上得岸时,转弯抹角,到了一个去处。引进几重门户,里头房室甚是幽静清雅。但见:
明窗净几,锦帐文茵。庭前有数种盒花,座内有几张素椅。壁间纸画周之冕, 桌上砂壶时大彬。窄小蜗居,虽非富贵王侯宅;清闲螺径,也异寻常百姓家。
原来这个地方是这缪浪儿一个囤子,专一设法良家妇女到此,认作亲戚,拐那一等浮浪子弟、好扑花行径的,引他到此,勾搭上了,或是片时取乐,或是迷了的,便做个外宅居住,赚他银子无数。若是这妇女无根蒂的,他等有贩水客人到,肯出一注大钱,就卖了去为娼。已非一日。今见春花行径,就起了个不良之心,骗她到此。那春花是个好人家儿女,心里尽爱清闲,只因公婆凶悍,不要说日逐做烧火、煮饭、熬锅、打水的事,只是油盐酱醋,她也拌得头疼了。见了这个干净精致所在,也不知好歹。那缪浪儿见人无有慌意,反添喜状,便觉动火。走到跟前,双膝跪下求欢。春花就变了脸起来:“这如何使得?我是好人家儿女,你原说留我到此坐着,报我家中。青天白日,怎地拐人来家,要行局骗? 若逼得我紧,我如今真要自尽了!”说罢,看见桌上有点灯铁签,捉起来望喉间就刺。缪浪儿慌了手脚,道:“再从容说话,小人不敢了。”原来缪浪儿只是拐人骗财,利心为重,色上也不十分要紧,恐怕真个做出事来,没了一场好买卖。吃这一惊,把那一点勃勃的春兴,丢在爪哇国去了。
他走到后头去好些时,叫出一个老婆子来,道:“杜奶奶,你陪这里娘子坐坐,我到他家去报一声就来。”春花叫他转来,说明了地方及父母名姓,叮嘱道:“千万早些叫他们来,我自有重谢。”缪浪儿去了,那老奶奶去掇盒脸水,拿些梳头家火出来,叫春花梳洗。立在旁边呆看,插一问道:“娘子何家宅眷?因何到此?”春花把上项事,是长是短, 说了一遍。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脚道:“这样老杀才不识人!有这样好标致娘子做了媳妇, 折杀了你,不羞?还舍得出毒口骂他,也是个没人气的!如何与他一日相处?”春花说着心事,眼中滴泪。婆子便问道:“今欲何往?”春花道:“今要到家里告诉爹娘一番,就在家里权避几时,待丈夫回家再处。”婆子就道:“官人几时回家?”春花又垂泪道:“做亲两月,就骂着逼出去了,知他几时回来?没个定期。”婆子道:“好没天理!花枝般一个娘子,叫地独守,又要骂他。娘子,你莫怪我说。你而今就回去得几时,少不得要到公婆家去的。你难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?这腌臜烦恼是日长岁久的,如何是了?”春花道: “命该如此,也没奈何了。”婆子道:“依老身愚见,只教娘子快活享福,终身受用。” 春花道:“有何高见?”婆子道:“老身往来的是富家大户公子王孙,有的是斯文俊俏少年子弟。娘子,你不消问得的,只是看得中意的,拣上一个。等我对他说成了,他把你象珍宝一般看待,十分爱惜。吃自在食,着自在衣,纤手不动呼奴使婢,也不枉了这一个花枝模样。强如守空房、做粗作、淘闲气万万倍了。”那春花是受苦不过的人,况且小小年纪,妇人水性,又想了夫家许多不好处,听了这一片活,心里动了,便道:“使不得,有人知道了,怎好?”婆子道:“这个所在,外人不敢上门,神不知,鬼不觉,是个极密的所在。你住几日。”春花道:“适间已叫那撑筏的,报家里去了。”婆子道“那是我的干儿,恁地不晓事,去报这个冷信。”正说之间,只见一个人在外走进来,一手揪住杜婆道: “好!好!青天白日,要哄人养汉,我出首去。”春花吃了一惊,仔细看来,却就是撑筏的那一个缪浪儿。春花见了道:“你到我家去报信吗?”缪浪儿道:“报你家的鸟!我听得多时了也。杜奶奶的言语是娘子下半世的受用,万全之策,凭娘子斟酌。”春花叹口气道:“我落难之人,误入圈套,没奈何了。只不要误了我的事。”婆子道:“方才说过的, 凭娘子自拣,两相情愿,如何误得你?”春花一时没主意,听了哄语,又且房室精致,床帐齐整,恰便似:“因过竹院逢僧话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”放心的悄悄住下。那婆子与缪浪儿两个殷殷勤勤,代替伏侍,要茶就茶,要水就水,惟恐一些不到处。那春花一发喜欢忘怀了。
过得一日,缪浪儿走出去,撞见本地方一个大财主,叫得吴大郎。那大郎有百万家私,极是个好风月的人。因为平日肯养闲汉,认得缪浪儿,便问道:“这几时有甚好乐地么?” 缪浪儿道:“我家有个表侄女新寡,且是生得娇媚,尚未有个配头,这却是朝奉店里货, 只是价钱重哩。”大郎道:“可肯等我一看否?”缪浪儿道:“不难,只是好人家害羞, 待我先到家与他堂中说话,你劈面撞进来,看个停当便是。”吴大郎会意了。缪浪儿先回来,见春花坐在房中,默默呆想。缪浪儿便道:“小娘子便到堂中走走,如何闷坐在房里?”杜婆子在后面听得了,也走出来道:“正是。娘子外头来坐。”春花依言,走在外边来。缪浪儿就把房门带上了,春花坐了道:“奶奶,还不如等我归去休。”奶奶道:“娘子不要性急,我们只是爱惜娘子人材,不割舍得你吃苦,所以劝你。你再耐烦些,包你有好缘分到也。正说之间,只见外面闻进一个人来。你道他怎生打扮?但见:
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中儿,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,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,青绒道袍儿,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,若非宋玉墙边过,定是潘安车上来。
他一直走进堂中道:“小缪在家么?”春花慌了,急掣身起,已打了个照面,急奔房门边来,不想那门先前出来时已被缪浪儿暗拴了,急没躲处。那杜婆笑道“是吴大郎,便不先开个声!”对春花道:“是我家老主顾,不妨。”又对吴大郎道:“可相见这位娘子。” 吴大郎深深唱个喏下去,春花只得回了礼。偷眼看时,恰是个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,心里看上了几分。吴大郎上下一看,只见不施脂粉,淡雅梳壮,自然内家气象,与那胭花队里的迥别。她是个在行的,知轻识重,如何不晓得?也自酥了半天,道:“娘子请坐。”春花终究是好人家出来的,有些羞耻,只叫杜奶奶道:“我们进去则个。”奶奶道:“慌做甚么?”就同春花一面进去了,出来对吴大郎道:“看得中意否?”吴大郎道:“奶奶作成作成,不敢有忘。”杜婆道:“吴大郎有的是银子,兑出千把来,娶了回去就是。”大郎道:“又不是行院人家,如何要得许多?”奶奶道:“不多。你看了这个标致模样,今与你做个小娘子,难道消不得千金?”大郎道:“果要千金,也不打紧。只是我大孺人狠,专会作贱人,我虽不怕她,怕难为这小娘子,有些不便,取回去不得。”婆子道:“这个何难?另租一所房子住了,两头做大可不是好?前日缪浪儿家有一所花园空着,要租与人, 老身替你问问看,如何?”大郎道:“好便好,只是另住了,要家人使唤,丫鬟伏侍,另起烟鬓,这还小事。少不得瞒不过家里了,终日厮闹,赶来要同住,却了不得。”婆子道: “老身更有个见识,你拿出聘礼娶下了,就在此间成了亲。每月出几两盘缠,替你养着, 自有老身伏侍陪伴。大郎在家,推个别事出外,时时到此来住,密不通风,有何不好?” 大郎笑道:“这个却妙,这个却妙!”议定了财礼银八百两,衣服首饰办了送来,自不必说,也合着千金。每月盘缠连房钱银十两,逐月支付。大郎都应允,慌忙去拿银子了。
杜婆转进房里来,对春花道:“适才这个官人,生得如何?”原来春花先前虽然怕羞,走了进去,心中虽还舍不得,躲在黑影里张来张去,看得分明。吴大郎与杜婆一头说话, 一眼觑着门里,有时露出半面,若非是有人在面前,又非是一面不曾识,两下里就做起光来了。春花见杜婆问她,她就随口问道:“这是那一家?”杜婆道:“是本地有名的财主吴家,号‘吴百万’吴大郎。他看见你,好不喜欢哩!他要娶你回去,有些不便处。他就要娶你在此间住下,你心下如何?”春花一了喜欢这个干净房卧,又看上了吴大郎人物。听见说就在此间住,就象是他家里一般的,心下到有几分中意。道:“既到这里,但凭妈妈,只要方便些,不露风声便好。”婆子道:“如何得露风声?只是你久后相处,不可把真情与他说,看得低了。只认我表亲,暗地快活便了。”春花强作应付,心里随机应变。
只见吴大郎抬了一乘轿,随着两个俊俏小厮,捧了两个拜匣,竟到缪浪儿家来。把银子支付停当了,就问道:“几时成亲?”婆子道:“但凭大郎尊便,或是拣个好日,或是不必拣日,就是今夜也好。”吴大郎道:“今日我家里不曾做得工夫,不好造次住得。明日我推说到杭州进香取帐,过来住起罢了。拣甚么日子?”吴大郎只是色心为重,等不得拣日。若论婚姻大事,还该寻一个好日辰。今卤莽乱做,不知犯何凶煞,以致一两年内, 就拆散了。这是后话。
却说吴大郎支付停当,自去了,只等明日快活。婆子又与缪浪儿计较定了,就拿了吴家银子一千两,给了春花银子二百两,其余摆将出来,摆得桌上白晃晃的,这光棍牙婆见了银子,如苍蝇见血,怎还肯人心天理?看官,有个缘故。他一者要在春花面前夸耀富贵,买下她心。二者总是在他家里,东西不怕他走趱那里去了,少不得逐渐哄的出来,仍旧还在。后来吴大郎相处了,怕她说出真情,要倒他们的出来,反为不美。这正是老虔婆神机妙算。
吴大郎次日果然打扮得一发精致,来缪浪儿家成亲。他怕人知道,也不用傧相,也不动乐人。只托缪浪儿办下两桌酒,请春花出来同坐。吃了晚饭进房。春花起初害羞,不肯出来。后来被强不过,勉强略坐得一坐,推个事故走进房去,关上房门,扑地把灯吹息, 提上包裹,推开后窗,从后窗跳下去,趁黑逃出狼窝。婆子还道:“还是女儿家的心性, 害羞,须是我们凑他趣则个。”移了灯,照吴大郎进房去。仍旧把房中灯点起了,移灯到床边,揭帐一看,不见踪影,以为藏在里屋,拿起灯,边喊边找人…… 一看里屋后窗打开,已知娘子逃走了,赶紧跑出来,抓住缪浪儿要人,缪浪儿吼道:“杜奶奶快寻人去……”真是:
新婚拒,婿家毒,物活重担压奴哭。
逃难又遭强歹赴。思乡路,施计跳出狼虎宿。
——南乡子
说话的,难道缪浪儿不见了媳妇就罢了,凭他自在那里快活不成?看官,话有两头, 却难这边说一句,那边说一句。如今且听说那严家。自从那日早起不见媳妇煮早饭,严婆只道又是晏起,走到房前厉声叫她,见不则声,走进房里,把窗推开了,床里一看,并不见春花踪迹。骂道:“这贱淫妇那里去了?”出来与严公说了。严公道:“又来作怪!” 料道是她娘家去,急忙走到渡口问人来。有人说道:“绝大清早有一妇人渡河去,有认得的,道是严家媳妇上筏去了。”严公道:“这妮子!昨日说了他几句,就待告诉她爹娘去。 恁般心性泼刺!且等她娘家住,不要去接她采她,看她待要怎的?”忿忿地跑回去与严婆说了。
将有一段时间,黎家宋女记挂女儿,办了几盒点心,差万春夫妇,到严家来问一个信。 严公道:“她归你家十来日了,如何到来这里问信?”那送礼的万春夫妇吃了一惊,道: “说那里话?我家姐姐自到你家来,才得两月多,我家又不曾来接,她为何自归?因是放心不下,叫我们来看望。如何反如此说?”严公道:“前日因有两句口斗,她使性子,跑了回家。有人在渡口见她的。她不到你家,到那里去?”那万春夫妇道:“实实不曾回家, 不要错认了。”严公炮燥道:“想是她来家说了甚么谎,您家要悔赖了别嫁人,故装出圈套,反来问信么?”那万春夫妇道:“人在你家不见了,颠倒这样说,这事必定跷蹊。” 严公听得“跷蹊”两字,大骂:“狗男女!我少不得当官告来,看你家赖了不成!”那万春夫妇见不是势头,盒盘也不出,仍旧挑了,走了回家,一五一十的对华国夫妇说了。宋女大惊,啼哭起来道:“这等说,我那儿敢被这两个老杀才逼死了?打点告状,替他要人去。”一面来与个讼师商量告状。
那严公、严婆死认定了黎家藏了女儿,叫人去接了儿子来家。两家都进状,都准了。
那保宁知府提一干人犯到官。当堂审问时,你推我,我推你。知府大怒,把严公夹起来。严公道:“现有人见她过渡的。若是投河身死,须有尸首踪影,明白是他家藏了赖人。” 知府道:“说得是。不见了人十多日,若是死了,岂无尸首?毕竟藏着的是。”放了严公,再把华国带上来。华国道:“知府大人,我在顺庆府李民圣大人足下为师爷,判过无数案件,你既不巡查,又不考究,随便带我上堂,是要触及刑法的,你这样办案,我要是一封家信寄与李知府,也许你吃不了兜着走,你想:人在他家,去了两月多,自不曾归家来。若是果然当时走回家,这十来日间严家何不着人来问一声,看一看下落?人长六尺,天下难藏。小的若是藏过了,后来就别嫁人,也须有人知道,难道是瞒得过的?老爷详察则个。” 知府像明白了什么,想了一想,道:“你说得是。如何藏得过?便藏了,也成何用?或是与人约定走了。”
严公道:“小的媳妇虽是懒惰娇痴,小的闺门也严谨,却不曾有甚外情。”知府道:“这等,敢是有人拐的去了,或是躲在亲眷家,也不见得。但人在你家,没有带好你媳妇,定是你老婆言语恶劣,或是太苛刻她,她受不了,才逃离你家,你严家责任重大,你推不得干净。赶快跟寻,同缉捕人役去追讨,限你十日,到期不御者,可要定你的罪啊!。” 又吩咐黎公道:“你也要协助缉捕人役共同办案。”严公押了。严公不见了媳妇,心中已自苦楚,又经如此冤枉,叫天叫地,没个道理。只得帖个寻人招子,许下赏钱,各处搜求,并无影响。且是那个聚龙湾严松不见了妻子,没出气处,只是逢五逢十就来禀官比较捕人, 未免严公陪打了好些板子。此事闹动了一个保宁府,城郭乡村,无不传为奇谈。真是,
春花逃婿家,禀报衙门判。严论有蹊闲,推理该堂断。
势将明道来,暗访寻真看。时复见光明,同共追根算。
——生查子
却说严家有个极密的内亲,叫做李小宝。偶然在阆中做买卖,闲游武庙街。只见一个娼妇,站在门首献笑,好生面染。仔细一想,却与春花一般无二。心下想道:“家里打了两年没头官司,她却在此!”要上前去问个的确,却又忖道:“不好,不好。问他未必说真情。打破了网,娼家行径没根蒂的,连夜走了,那里去寻?不如报她家中知道,等他自来寻访。”来到严家,一一与严公说知。严公道:“不消说得,必是遇着歹人,转贩为娼了。”叫其子严松,密地拴了百来两银子,到阆中武庙街赎身。又商量道:“私下取赎, 未必成事。”又在保宁府告明缘由,使用些银子,给了一张广缉文书在身,倘有不谐,当官告理。严松听命,严公就央了李小宝作伴,一路往阆中来。那李小宝自有旧主人,替严松另寻了一个店楼,安下行李。李小宝指引他到这家门首来,正值他在门外。严松看见果然是春花,连呼他小名数声;那娼妇只是微微笑看,却不答应。严松对李小宝道:“果然是我妻子。只是连连叫她,并不答应,却象不认得我的。难道在此快乐了,把个丈夫都不招揽了?”李小宝道:“你不晓得,凡娼家龟鸨,必是生狠的。你妻子既来历不明,她家必紧防漏泄,训戒在先,所以她怕人知道,不敢当面认帐。”严松道:“而今却怎么通得个信?”李小宝道:“这有何难?你做个要嫖她的,设了酒,将银一两送去,外加轿钱一包,抬她到下处来,看个备细。是你妻子,密地相认了,再做道理。不是妻子,放她去罢!”严松道:“有理,有理。”李小宝在阆中久做客人,都是熟路,去寻一个小闲来,拿银子去,霎时一乘轿抬到下处。那李小宝忖道:“果是他妻子,不好在此陪得。”推个事故, 走了出去。严松也道是他妻子,就很随便,却也不留李小宝。只见那轿里袅袅婷婷,走出一个娼妓来。但见:
一个道是妻子来,双眸注望;一个道是客官到,满面生春。
一个疑道:“何不见她走近身,急认丈夫?”
一个疑道:“何不见他迎着轿,忙呼姐姐?”
却说那严松向前看看,分明是妻子。那娼妓却笑容可掏,佯佯地道了个万福。严松只得坐了,不敢就认,问道:“姐姐,尊姓大名,何处人氏?”那娼妓答应“姓张,小字月华,是本处人氏。”严松看她说出话来是阆中口音,声气也不似春花,已自疑心了。那张月华就问严松道:“客官何来?”。严松道:“在下保宁府聚龙湾严某,父某人,母某人。” 恰象那查他的脚色,三代籍贯都报将来。也还只道果是妻子,她必然承认,所以如此。那张月华见他说话牢叨,笑了一笑道:“又不曾盘问客官出身,何故通三代脚色?”严松满面通红,情知不是春花了。摆上酒来,三杯两盏,两个对吃。张月华看见严松,只管相他面庞一会,又自言自语一会,心里好生疑惑。开口问道:“奴自不曾与客官相会,只是前口门前见客官走来走去,见了我指手点脚的,我背地同妹妹暗笑。今承宠召过来,却又屡屡机觑,却象有些委决不下的事,是什么缘故?”严松把言语支吾,不说明白。那张月华是个久惯接客,乖巧不过的人,看此光景,晓得有些尴尬,只管盘问。严松道:“这话也长。”严松喝了酒,很随和抱住张月华在床上睡了,做了一番魂云颠倒的事。
那张月华又把前话提起,严松只得告诉她:家里事如此如此,这般这般。“因见你厮象,故此假做请你,认个明白,那知不是。”月华道:“果然象否?”严松道:“举止外 像一些不差,就是神色里边,有些微不象处。是至亲贴身终日在面前的,用意体察才看得出来,也算是十分象的了。若非是声音各别,连我方才也要认错起来。”月华道:“既是这等厮象,我就做你妻子罢。”严松道:“又来取笑。”月华道:“不是取笑,我与你熟商量。你家不见了妻子,如此打官司不得了结,毕竟得妻子到了官方住。我是此间良人家 儿女,在王秀才家为妾,大娘不容,后来连王秀才贪利忘恩,竟把来卖与这张妈妈家了。那龟儿、鸨儿,不管好歹,动不动非刑拷打。我被他摆布不过,正要想个讨策脱身。你如今认定我是你失去的妻子,我认定你是丈夫,两一同声当官去告理,一定断还归宗。我身 既得脱,仇亦可雪。到得你家,当了你妻子,官事也好完了,岂非万全之算?”严松道: “是到是,只是声音大不相同。且既到吾家,认做妻子,必是父母处明白,方象真的,这 却不便。”月华道:“人只怕面貌不象,那个声音随他改换,如何做得谁?你妻子相失两年。
假如真在聚龙湾,未必不与我一般乡语了。亲戚族属,你可教导得我的。况你做起事来,还等待官司发落,日子长远,有得与你相处,乡音也学得你些。家里事务,日逐教我熟了,有甚难处?”严松心理先只要家里息讼要紧,细思月华说话尽可行得,便对月华道:“吾随身带有广缉文书,当官一告,断还不难。只是要你一口坚认到底,却差池不得的。” 月华道:“我也为自身要脱离此处,趁此机会,如何好改得口?只是一件,你家妻子是何等样人?我可跟得她否?”严松道:“我妻子是个老实人。
你与她性格像好。”月华道:“凭她怎么,毕竟我似为娼。况且一夫一妻,又不似先前做妾,也不误了我事了。”严松又与她两个赌一个誓信,说:“两个同心做此事,各不相负。如有破泄者,神明诛之!”两人说得着,已觉道快活,又弄了一火,搂抱了睡到天明。
严松起来,不梳头就走去寻李小宝,连他都瞒了,对他说道:“果是吾妻子,如今怎处?”李小宝道:“这行院人家不长进,替他私赎,必定不肯。待我去纠合本乡人在此处的十来个,做张呈子到知府处呈了,人众则公,亦且你有本府广缉春花文书可验,怕不立刻断还?只是你再送几两银子过去,与他说道:“还要留在下处几日。’使他不疑,我们好做事。”严松一一依言停当了。李小宝就合着一伙阆中人同严松到府堂,把前情说了一遍。严松又将府间广缉文书当堂验了。知府立刻签了牌,将张家乌龟、老妈都拘将来。张月华也到公庭,一个认丈夫,一个认妻子。那众阆中人除李小宝外,也还有个把认得春花的,齐声说道:“是。”那乌龟分毫不知一个情由,劈地价来,没做理会,口里乱嚷。知府只叫:“拿嘴!”知府断严松出银四十两还她乌龟身价,领妻子归家。那乌龟买良为娼, 问了应得罪名,张月华一口怨气先发泄尽了。严松欣然领回下处,多完备了,然后起程。这几时落得与月华同眠同起,见人说是夫妻,枕边絮絮叨叨,把说话见识都教道得停停当当了。
在路不一日,将到聚龙湾,有人见他夫妻一路来了,拍手道:“好了,好了,这官司有结局了。”有的先到他家里报了的,父母俱迎出门来。那月华装做个认得的模样,大刺刺走进门来,呼爷叫娘,都是严松教熟的。况且娼家行径,机巧灵变,一些不错。严公道:“我的儿!那里去了这么多天?累煞你爹也!”月华假作硬咽痛哭,免不得说道:“爹妈这几时平安么?”严公见他说出话来,便道:“去了这么多天,声音都变了。”严妈伸手过来,拽她的手出来,抢了两抢道:“我数落了几句,你就出逃,还跑到妓院当窑子,太没良心。”只有严松与月华心里自明白。严公见媳妇回来了,心里放下了一个大疙瘩,那里还辨仔细?况且十分相象,分毫不疑。至于来踪去迹,他已晓得在娼家赎归,不好细问得。
第二天,严公差佣人到黎家请了华国夫妇。
隔了两日,知府升堂,正待把严家这宗文卷注销立案,只见黎家华国夫妇来告道:“昨日严家领去的,不是我大女儿春花。”那知府大怒道:“好个刁民!严松已认你女儿是他妻子,怎么的不是你女儿?,如何还不肯休歇?”喝令扯下去遭打。那华国叫道:“知府大人,你办案纯属不知底细,听信一面之词,不做调查思考,硬说这面貌相同道是他的妻子,相象是要得紧,她的心底记忆就不同了,我到他家,她并未知我家底细,这哪是我女儿呢?经我亲自派员调查,此女子名叫张月华,她是本地良人家儿女,在王秀才家为妾, 大娘子不容,后来王秀才贪利忘恩,竟把她卖与这张妈妈家了。那龟儿、鸨儿,不管好歹,动不动非刑拷打。被她摆布不过,想个讨策脱身,谁知严松认定是他失去的妻子,两人一同声当官去告理,一是既得脱身,二是仇亦可雪,当了严松妻子,官事也好完了,岂非万全之算?”
知府道:“真是这样吗?”华国道:“升堂拷问便知” 知府立即升堂,道:“传严家严松及假春花到堂。”知府道:“你们欺瞒本官,严松,这女子不是你妻,为啥硬说是你妻子,快快招来!”严松心里无底,这是谁泄了密,眼睁睁看着张月华,“镗”的一声, 知府怒道:“你不承认推出去叫打!”严松熬不过,只好一五一十招认了。
知府听了华国的计谋,这才分忖该房写告示出去遍贴,说道:“黎春花已经某月某日追寻到官,两家各息词讼,无得再行告扰!”却自密地悬了重赏,着落应捕十余人,四下分缉,若看了告示,有些甚动静,即便体察,拿来回话。真是:
案奇真个蹊跷幻,恼乱得、使人玄乱。
醉归来、恰似出容同,但自断、严松出乱。
谁知随妓归云串,好作个、鸳鸯活灿。
照月华,匀扮面,假真颜;算终办、颠鸾完善。
——步蟾宫
不说这里探访。且说春花自逃出缪浪儿家,缪浪儿率十多名家丁,连夜连晚到处找寻。
且说春花背着包裹,跳窗而逃,人生地不熟,趁晚朝山脊而跑,她不断的向前跑着,汗一滴一滴从脸颊上落下,衣服也因摔了跟头的缘故,显得有些破烂。但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,向前跑,向前跑,他的潜意识不断告诉自己,一定要离开魔掌,一定要离开那个鬼地方!渐渐的,他跑不动了,只能疾步走着,脸色极其苍白,远处,传来了寻找她的人的灯笼火把和喊叫声音,他是第一次逃跑,因为她怕失去名节,至于节操,她看得很重,作为严松的妻子,从未失去贞节,她到严松的第一天,意识到严家子弟畏惧,懦弱,贪欲, 做人不厚道、无气度,对人说三道四……我与他家处不了关系,严松又是个软骨头,无主见, 硬谈不上夫妻,必须逃离苦海,一早到了渡口,见了缪浪儿的筏子,哪知上了筏子就上了贼船,只有温存寻找机会……一群恶狼愤怒地追杀她,然而她开始狂奔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?这就是潇洒!想逃命,跑的再快也有可能被人家围追堵截,但是花式逃跑可就不一样了。她跑得太吃力了,她躲在悬崖树脚下休息了片刻,见追赶的人踪迹渐来稀远了,才慢慢地从树脚下爬上来,趁黑继续前进。
约行了三十里许,不多时,银箭般的雨点,虽不能说倾盆下注,却也使她感到难堪,头上,手上,身上,都密布了一颗颗的水滴,由于雨的威胁,又处于荒野之地,只得把头紧紧的俯着,任其欺凌。她不禁笑说:“哈哈,真是所谓露宿风餐呢!”。
灰暗的水面,渐渐开朗,黎明久雨的天空,蔚蓝色出现。可爱美丽的自然界!稍息后, 又匆匆上道,羊肠曲折,道旁树木丛生。冷风吹得紧,两手冻得红萝卜似的,正扬意走上回娘家的路上,谁知从山坡上冲下几个彪形大汉,连扯带拉抬上山顶。原来 ,这是鼓罗山寨一群匪徒,寨主名叫杜白狼,经常抢窃单身妇女,漂亮的被糟蹋,不如意者当面释放。这杜白狼一看春花,光洁白皙的脸庞,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;乌黑深邃的眼眸,泛着迷人的色泽;那浓密的眉,高挺的鼻,绝美的唇形,无一不在白狼心里神魂颠浪,早看得入迷了。立即吩咐左右退下,亲自上前,端出凳子请她上座……
这春花一贯是巧施计谋,硬着陆是要吃亏的,只有伏伏贴贴听他的,寻找机会逃跑。
杜白狼让春花坐在凳子上,一把将春花抱在怀裡,也不整个抱起,索性坐下来,拥著美人儿的腰来回抚摸,那春花气喷地用手给了一个耳光:“好哥哥情急不在今天?待明日再说……”随着她双手捂着头,号声大哭起来:“我苦命啊!呜呜呜呜呜……被抢到这个鬼地方……”
她怒火冲天地望着白狼,这白狼手足无措,反而给她道歉:“对不起呀对不起呀,你别哭了呀!”
春花哭了很久,眼睛都哭红了,这白狼也劝得累了,索性就让她哭,等她哭得一双眼睛都肿得像个桃子一般时候,她才停了下来恶狠狠地望着白狼,如果你再对我无礼,我就哭死你!白狼连连点头:“不无礼了,只要你不哭就好了。”
春花在山寨折腾了两年时间,天天装疯,傻笑,嚎哭,弄得白狼和群匪不得安宁。
有一天天还没亮,春花爬起来走到一处空地放开嗓子嚎,把大伙通通吵得没法睡,哭完了又开始唱哀调,谁一靠近她就咬谁,跟个小疯狗一样。这不打紧,山寨做饭用的薪柴, 她不知浇了什麼水在薪柴上,弄得生火用的柴禾全部湿湿黏黏,晒也晒不干,一碰火就直冒黑烟,让他们晚膳也没法做,还得重新去捡木劈柴。
“爷儿们,这孬种是个疯子,把她关在柴房里,由二狗守护,不能让她跑了!今晚无柴火不能做饭,爷就不信有钱还找不到个顺服的,走,咱们下山逛窑子去!”
白狼作为大当家,怎麼也不想让春花撒野,摆明了要和她杠到底,大手一挥就招呼兄弟们出寨寻乐。
难得大当家说要拿寨里的积蓄让大家享受,这群老粗们自然不会放过机会,谁知进到镇里,却没一家秦楼楚馆愿意接他们的客。最后好不容易拿出锦春堂山寨的名号,强迫性的拿下间窑子来做乐,一人点了一个花姑娘好不开心。
而在他们下山的这段时间,春花一心想逃出寨窝,看见二狗守在柴门前,她移到二狗门旁,殷勤的招呼道:“二哥哥,你好老实啊!你把柴门开了,我俩一起玩,好吗?”“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狐狸精,男人看见都会着迷的,我才不会上当呢!”二狗心里是那样说,但内心还是……
春花笑笑,“我才不想做狐狸精,狐狸精多讨厌呀,要我做,我就做仙女。”二狗没说什么,只是觉得春花的态度改变了,不过她为什么会变,二狗却是一点都不晓得。
春花娇气的劝二狗,“你在外面好冷啊!把门开了进来嘛,我是不会跑的,你想,半夜三更,又往何处跑勒?” 二狗想:他们都出去快活,我一个男子汉,害怕这娇滴滴的女子吗?
二狗开了门,在灯光下见春花浑圆的屁股,一时间起了坏心,忍不住去摸了一把。很肥很滑腻。二狗挑起她的一缕青丝放在鼻子底下闻着,春花故意手脚发软动弹不得,见他举止轻浮气恼道,“滚开!”
绝色就是绝色,竟然连生气都那么的勾人。春花不禁笑道,“我何德何能竟能与你做一夜夫妻?”
“今日有此殊荣,定要卖力伺候公子舒服才是。”二狗听她说的下流,二狗却不急着动手,坐在她身边凑过脸去在她勃颈上嗅了嗅,“真香,是天外进贡的美人面。”
二狗并不知那些香料的来头,瞪着春花道,“你碰我一下吧,这香太浓了”
春花哈哈大笑,“二哥哥追随你真是让我感动,你有这样的情分做过一次夫妻也值了。”
春花故意把迷魂香凑到二狗极厚的脸皮上,二狗不通情事被她几句逗弄的蜜语使二狗面色通红。知道此刻危急万分,说些话也无力了,他明知上当,但力不从心,迷昏倒了。春花搭着包裹,趁黑逃出寨窝。
且说阆中天宫院有一位秀才,姓杨名聪,他丰姿英伟,耸壑昂霄。步履端祥,循规矩尧。语言遵孔孟,礼貌体周苗。他文采飞扬,出口成章,风神超绝 。这天晚上,睡梦中见一位美貌女子,就是东南西北也找不出这个绝色来,由不得浑身酥软,心中沉醉,急急抢步向前,把美人的袖子扯住,问道:“美人住居何处,姓什名谁,青春多少,可曾婚聘?”那女子回道:“奴住阆中升钟回龙黎家坝,姓黎名春花,乳名春儿,年方十七,虽已适人, 未曾同阁。今落难锣鼓寨。”那美人甩开衣袖,匆匆跑走了,他一边喊一边追,冷不防一个跟头,摔下山崖,猛地一惊,才是南柯一梦,他坐在床上,心中一想:“此梦好奇遇也!美人明明说了名姓地方,他不敢耽搁,等不得天亮,带了两名跟班,上马离家。朝鼓锣山寨而去。
在路不到一个时辰,到了鼓锣山下,他们下马仔细找寻,还是跟班发现悬崖下一女子, 已是昏迷不醒,遍体鳞伤,原来才是春花离开山寨,又不知路径,只顾往前跑,不慎摔下山崖的。杨聪扶起春花,抱在马背上,飞马回到家里。经郎中治疗,很快清醒过来。春花看到床边的少年,一表人才、风度翩翩,衣冠楚楚、相貌堂堂、眉清目秀、容光焕发、明眸皓齿,便问道:“这在哪里?怎么会睡在你床上?”说着,便起身离开。这时,杨聪一家人都来了,说明了情况,春花才安下心来养伤。
不到十天,春花的伤痊愈了,当春花梳洗着装出现在杨聪眼前:身材高桃,体态轻盈,举止端庄娴雅。乌发如漆,肌肤如玉,美目流盼,一颦一笑之间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风韵。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,美而不妖,艳而不俗,千娇百媚,无与伦比。那杨聪傻了眼,看呆了。春花施礼道:“谢谢恩公!”“不用谢!不用谢!”于是上前扶她,春花面前的他:肤色白皙,五官清秀中带着一抹俊俏,乌黑深邃的眼眸,泛着迷人的色泽;那浓密的眉,高挺的鼻,绝美的唇形,无一不在张扬着高贵与优雅,这,这哪里是人,这根本就是童话中的白马王子嘛!春花从来未有的感觉才真正有了依靠。“我要回家,你愿送我吗?”
“我当然愿意!”这也是杨聪从未有甜蜜,对春花百般依顺。杨聪的父母打心眼里是高兴的,有了这样的媳妇,是杨家八辈子的福。
春花回家时,早安排杨家跟班到黎府报信。临行时,杨家父母目送一里之遥,杨聪春花一路上男欢女迎,你说我笑,好不甜蜜,当杨聪问:“人生中什么事情最美丽?”春花道:“莫过于遇见你。” “人生中什么事情最奇迹?” “莫过于拥有你。” “人生中什么事情不能忘记?” “那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不分离!” ……
不知不觉到了黎府大院,华国全家人出院迎接,两年不见,母女抱头痛哭……还是大家劝说,转悲为喜,今天团聚,双喜盈门,女儿女婿回家,请了黎姓亲房为新婿女儿贺喜不提。 真是:
幻梦秀才鸳鸯有,摔岩春花可知谁。
落寞魂游引情侣,费尽平生相思归。
昼有所思入境界,夜无想睡意朦追。
此别如今成双对,天生姻缘两相随。
这里却说缪浪儿 一日在外行走,闻得保宁府前出告示,道黎春花已寻见之说。急忙来对杜婆说:“不知那一个顶了缺,我们这个货,虽然逃了,我们该无忧了。”杜婆不信, 要探个实在。一同来到府前,看了告示。缪浪儿未免指手划脚,点了又点,念与杜婆听。早被旁边应捕看在眼里,尾了他去。到了僻静处,只听得两个私下道:“好了,好了,而今睡也睡得安稳了。”应捕忽地跳将出来道:“你们干得好事!今已败露了,还走那里去?”缪浪儿慌了手脚道:“不要恐吓我!且到店中坐坐去。”一同杜婆,邀了应捕,走到酒楼上坐了吃酒。缪浪儿推讨嘎饭,一道烟走了。单剩个杜婆与应捕处了多时,酒肴俱不见来,走下问时,缪浪儿已去久了。应捕就把杜婆拴将起来道:“我与你去见官。”杜婆跪下道: “上下饶恕,随老妇到家中取钱谢你。”那应捕只是见他们行迹跷蹊,故把言语吓着,其实不知甚么根由。怎当得虚心病来。应捕料得有些滋味,押了她不舍,到府衙问话。
却说缪浪儿自酒店逃去之后,撞着同伙张牛儿,一同作伴,到嘉陵江渡口。正见自家丫头在江边洗裹脚,一手扯住她道:“你是我家使婢,逃了出来,却在此处!”便夺她裹脚,拴了就走。要扯上竹筏,那丫头大喊起来。缪浪儿将袖子掩住她口,丫头尚自呜哩呜喇的喊。张牛儿便一把掐住喉胧,用得手重,口头又不得通气,一霎鸣呼哀哉了。地方人走将拢来,两个都擒住了,送到府里。
正值春花、杨聪回了家,和父母一起来到府堂。过堂之时,春花数列她的遭遇,连知府也为之感动。那知府极是个正气的,见了缪浪儿,大怒道:“缪浪儿是首恶。”喝交皂隶,重责六十板,当下绝气。知府当堂宣布:“严松认假作真,判拐骗人口罪,边境充军;张牛儿掐死丫鬟,判处死刑,张月华由严家用价赎身,跟随严松……”。只有吴大郎广有世情,闻知事发,上下使用,并无名字干涉,不致惹着,朦胧过了。
知府走到华国面前,与华国商好后,当面做主,就在知府大堂为春花杨聪举行了婚庆典礼。真是:
勾魂落魄寻仙妍,雨露含情找妹甜。
梦幻留香貌绝世,君郎抱枕彩蒂莲。
红枝物润竞娇女,蝶泳桃红恋意绵。
自古相思心意至,如今府第誓婚权。
春花和杨聪回到天宫院,夫妻二人男耕女织,勤俭为家,后生三男两女,夫妻长命百岁,杨聪八十而终,春花八十六岁而终,这是后话不提。